《海拉尔的三行诗》最新免费章节第一章
第一章
“哎,哎,小六,醒醒,别睡了!咱们到了!快看快看,那边儿有好大一群羊啊!”
“嗨!这才几只啊!内蒙古草原上羊多的是呢!哎,清哥,你是不是没见过活的羊啊?还是这么大一群!”
“我长这么大,也没在国内玩儿过几个地方,还真是第一次见着这么多羊!哎,阿景,阿景,你说这么些羊,要是都抓了来,在咱家门口开一炭火涮羊肉,这不得把东来顺都挤兑黄了?”
“好。”
“景行你可算了吧,就你顺着他,他说什么你都说好,哎,不是我说你,人家东来顺百年老店,你在内蒙带一车羊回去就能比人家正宗了?就你这异想天开的,改天是不得把园子拆了换成麻将馆了?”
“嘿!思昭,还真让你说着了,我就说广德楼平时单能吃饭喝茶业务太单一了,工作日的时候攒底都没剩几个人看,要是再辟出俩单间摆上麻将桌,这不是能提高上座率嘛!”
“去你的,生意都做到园子头上来了。火车上你倒是睡得熟,四仰八叉的跟个八爪鱼似的往两边儿人身上抓,关逾明可是一直没合眼,人家好不容易能休息一会儿,你又吵他。”
“哪儿有,我跟小六一块儿长起来的,他睡得少而且觉浅,睡一会儿就精神了,是不?小六?关小六?”
“你让他睡着,干嘛叫……”
有只散发着洗衣液的干净香气的手伸过来在关逾明的颈侧拍了拍,指尖刮过他的脸颊,惹得关逾明背后汗毛倒竖浑身猛地僵住。他在心里默数了三个数,放松手臂坐直了身体,抬手轻轻揉了两下眼睛。
“没事,小师叔,”他睁开眼睛适应车里的光线,眼周的肌肉收缩了几下,瞳孔慢慢收缩,凝聚起视线的焦点,“我醒了。”
“我就说他睡醒了嘛,”放在他颈侧的手收了回去,手的主人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两道剑眉透露出英气,双眼像新月一般弯着,眼尾稍稍挑上去,流畅得仿佛是沾墨的湖笔勾勒出了线条,他坐在商务车中间一排的座椅上,探身凑到关逾明面前,笑盈盈地看着他,露出两排白玉一般的牙齿,“小六小六,你看窗外的草原,彭越家的马场跟这儿比简直就是手巾板儿!一会儿到了住处,咱跑马去吧!我跟你说跑马这事儿我太在行了,哎,你记不记得那回在彭越家跟大白赛马,那会儿我骑的是小马,大白骑的那可是纯种的伊犁马,他都没跑过我,这回来草场上我跟你赛一回!”
“哎我说清哥,”坐在副驾驶上的男人看上去至多不过二十七八,眉目很是清秀,口音里夹杂着一些江南腔调,关逾明看着他鼻尖上的一颗小痣,恍惚了片刻才认出来这是同行的宋思昭,是一个歌剧演员,虽然生长在上海,但是因为工作原因一直常住北京,听说和刚才叫醒他的小师叔俞幼清有些交情,两个人最初是酒友,认识的年头已经很不短了,这一次来内蒙古旅游,也是他组织起来的,“你骑术这么好呢?待会儿也教教我呗!”
“那没问题啊,我跟你说,思昭,骑马这件事儿呢,其实很简单,但是你得有天赋知道吧?要是你跟这马有缘分,那你俩妥妥的天作之合,那要是没缘分,他不给你摔个腿断胳膊折都是便宜你了……”
关逾明深知他这位小师叔倘若打开了话匣子,说不完肚子里的话嘴是闭不上的,于是抬手捂住一个哈欠,扭过头去看窗外。他坐在最后一排的行李堆里,紧贴着车窗坐得端正,稍微侧身就能看见窗外碧绿一片漫无边际的草场和半山坡上一团一堆聚在一处的羊群。远处青蓝色的山峰隐在舒卷的云雾中,高远得如同可望不可及的仙境一般。
这是关逾明第四次来内蒙古了。
五岁那年夏天他跟着父母来过一次,在短短三天里被呼伦贝尔草原上凶猛硕大的蚊子叮咬得浑身红肿,坐在回北京的火车上哭了一路。额头正中央一个足有鹌鹑蛋大小的包红得发紫,又疼又痒,他总要伸手去抓却被父母强行掰过两只小手扭在背后。他不敢哭出声,扁着嘴不吭气,眼泪不停地滚落下来。邻座的中年男人看他哭得满脸是泪,从包里拿出一小盒止痒消肿的草药膏递给父母,说草原上的蚊子凶得很,小孩子身体弱,普通的药膏是不管用的,要涂他们草原人用的东西,睡一夜就能消肿了。
清苦的草药膏抹在额头上像无数根针扎进去一样细密地疼,关逾明攥着用红绒绳挂在脖子上的玉观音挂坠没有忍住哭出了声,他没有大声哭喊,只是咬着嘴唇不停地小声啜泣。祖父常教导他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不可放肆情绪,他记得很牢,掉眼泪也不想让别人看见,脱掉鞋子蜷缩在火车座椅的一角环抱着手臂把眼泪和疼痛一齐藏起来。
关逾明依稀记得火车到站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他睡得迷迷糊糊被父亲抱在怀里下了车,身上围着一件薄外套,外套散发着和母亲身上一样的花果香气,浅淡清新,就像他优雅秀美的母亲。他在父亲的怀里睡着,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在家里,浅色的床帐有一半垂落下来,把蚊帐包裹在里面,挡住耀眼的阳光。
那是关逾明离父母最近的一次。他们就像是关逾明生命中的一个符号,代表着两个与他血脉相连的人,而不是像隔壁胡家的那对每天都抱着孩子出门,或者坐在胡同口的槐树下陪孩子玩的年轻小夫妻。关逾明有时候被祖父牵着去逛琉璃厂,路过胡同口的时候能看见那对和他父母年纪相仿的夫妻拿着玩具逗弄怀里的孩子,或者推着儿童车带着他们的小儿子慢慢悠悠地散步。关逾明很少去看他们,总是牵着祖父的手目不斜视地走过去。几年后他上了小学,祖父便不再牵着他出门了,他背着书包跟在祖父身后,依旧会经过胡同口,碰见胡家的三口人和其他街坊在一处聊天喝茶。
他还是不去看,也不去听他们说些什么。
火车上热心善良的草原汉子送他的药膏见效很快,回到家里的第二天,关逾明身上的红肿已经消失了大半。四九城炎热的夏天结束后,父母再一次变得忙碌,见面的机会寥寥无几,往往是年节或亲友生日的家宴上父母才有时间和他坐在一起,陪他吃上一顿饭,给他添菜挑鱼。读小学前父亲总要考他背书,《论语》里随意抽一篇让他背诵几句,有时候也考诗词,那时还只是背诵,读书的时候不仅要背还要释义。母亲待他要宽松些,会问几句衣食住行的细节,听他讲学校里的事情,寥寥几句听完她也像很开心似的,会抚着他的脸颊轻声和他说话,分别的时候吻在他的额头上。他不很习惯,起初身体总僵着,次数多了也就释然,再大些的时候就学会了回吻一下母亲的脸颊,像模糊的婴儿时期感受到的一样,轻声说一句“Maman ,je t’aime”。那种时候母亲总是很高兴,漂亮的眼睛里像是蓄满了泪水,但是她总是笑着的,就像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她抱着关逾明坐在蒙古包前给他唱古老的民谣的时候一样。
高中毕业那年关逾明一个人在内蒙古的草原上住了半个月,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又一个人背着包来了一次。他总能在悠远的长空下澄澈清明的海子边枕着油绿的青草睡过去,一直到入夜起风的时候才醒来,看着满天星星爬上深色的天幕。草原上的风有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和四九城里春日的黄沙漫天全然不同,刮起来就要抵挡一切似的,关逾明偶尔会坐在草坡上看远处的牛羊和跑马的牧民,一看就是一整天。那时候经常借宿的牧民家里经常有人来串门,听说他是从首都来的汉人孩子,总要问他一些关于所谓“中土风物”的问题,手机和网络还是不足以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关逾明总是回答得很简单,后来主人家的额吉大约是觉得他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一到家中有客人来,就给他装上一壶奶茶让他到草场上去看跑马。奶茶他是喝不惯的,但是早起出门时慈眉善目的额吉给他带上满满一壶,傍晚时分他总是带着空壶回来。
离开内蒙回北京的时候他付清了旅费之外,又把自己手腕上带来的手表留给了主人家的阿爸,算作临别的礼物。从那年夏天之后,关逾明再也没有来过内蒙古。他从前不爱和别人一块儿出门,这一次实在是盛情难却,再加上小师叔俞幼清软磨硬泡生拉硬拽,他想到自己确实刚刚大学毕业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就简单打点了行囊跟着小师叔一行人登了开往内蒙的火车。
这一带的草场关逾明没有来过。他一个人去过不少牧区,但是都在极偏远的地方,许多当地牧民基本上不懂汉语,交流起来很困难,草场的生态很原始,长空万里,水草丰美,牧民偶尔还能猎到獭子。獭子肉质肥美,整只夹在烤了,撒上粗盐,香味醇厚油脂丰沛,关逾明有幸吃过一次,即便他几乎从不吃肉也对那种滋味记忆犹新,可惜这些年来草原的生态状况改善的情况不容乐观,原先驰骋在高原上的狼群早已销声匿迹,连獭子也被牧民们抓来吃得干净,有时一年也见不着一只,纵使牧草长得再丰美,最初的生态已然回不来了,獭子肉倒成了稀罕物,偶尔能抓到烤来吃,比羊肉还金贵。
车窗狭小视野受限,目之所及的草场一片和美,关逾明望着油绿的草原出神,一直平稳行驶的商务车突然猛地一耸,然后速度慢慢减缓,最后停了下来。
“哎,到了到了!阿景,小六,咱们下车喽!”
俞幼清嘴里喊着,抓起墨镜架在鼻梁上,连外衣也不穿,半敞着衬衫的领口就拉开车门跳了下去。原本坐在他身边的青年人从头到脚丝毫不乱,衣衫上不见一丝褶皱,方领T恤一直扣到了最顶端。俞幼清迫不及待地跳下了车,他并没伸手阻拦,只是默默地拿起俞幼清落在座椅上的外套一言不发地也跟着下了车。车里这时只剩下了关逾明自己,他撑着座椅伸直腰背,伸手去摸开关,却发现门正敞开着,他被成堆的行李堵在角落里,连移动手脚都困难,要是变成一只苍蝇,勉强还能飞过去。
他料想这一车的人都要先安顿下来再做打算,行李总要搬到住处去,于是别扭地挪了挪腿,等着已经下车的人过来搬行李,再不济开了后备箱他也能顺着缝隙爬出去。
过了足有五分钟,关逾明迷迷糊糊地听到一声闷响,睁开眼一看,车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关上了,他愣了片刻,立即明白过来自己是被锁在了车里,神智顿时恢复了清醒。他侧头看了看窗外,只有大片的草场和远处的牛羊,于是毫不迟疑地抬手敲了敲玻璃,扬声喊道:“师叔?景哥?宋大哥?陈彻大哥?有人在吗?有没有人在?”
他来来回回喊了几遍,没人应声。关逾明伸手去摸手机,按了几下屏幕手机依然漆黑一片,他这才想起来坐在火车上俞幼清闲无聊又觉得他自己的手机性能不够好,拿着关逾明的手机玩了一路却忘了帮他充电,这时候想开机是不可能的。关逾明攥着拳头思索了几秒,伸手从行李堆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抽出了一根棒球棍,拿在手里掂了掂分量。
这跟棒球棍是俞幼清随身带来的,他最近迷上了打棒球,在北京城里总嫌地方小,一听说要到内蒙草原,觉得天高地阔场子要多大有多大,于是兴高采烈地背来了全套棒球装备。他从小点子就多,想起一出是一出,和他一块儿长大的发小景行跟他性子全然不同,却最能由着他折腾。俞幼清要打棒球,他就陪着一起练,顶着大太阳在棒球场上跑来跑去。去年夏天俞幼清突然喜欢上潜水,拉着景行一起考了潜水资格证,两个人也是有钱有闲,整整两个月满世界溜达,就为了找地方潜水看海。最离谱的一次是俞幼清读高二那年寒假,他们俩攒了小半年私房钱,最后瞒着父母跑了一趟阿尔卑斯山,在冰天雪地里呆了一周,就为了俞幼清一句“我肯定得把滑雪学会,以后去挪威玩儿”,回国以后俞幼清倒是没怎么着,活蹦乱跳,能吃能睡,景行却大病了一场,一直高烧不退。最后感染了肺炎,在医院又住了半个月。但是这也没挡住俞幼清上山下海的脚步,景行也是舍命陪君子,这些年两个人东游西逛,全世界的大好河山几乎看遍,就把眼光又收回到国内,前不久刚去过九寨沟,回到家里休息了一周,就又到了内蒙古。也多亏他是这么个异想天开的性情,不然关逾明在车里恐怕不等有人来也就耗尽了氧气,被憋死在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场上了。
棒球棍拿在手里的分量不轻,关逾明估算了一下这台商务车的抗损性能和维修费用,伸手在玻璃窗上摸索了一会儿,找到最薄弱的位置,在狭窄的空间里勉强竖起球棍对准他选好的位置,尽可能地举起手臂。
“我就说你们不是五个人嘛,这才四个下了车,哎,你……”
车门被猛地拉开,关逾明吓了一跳,连忙收住力气,手里的棒球棍在距离车窗不到两公分的位置勉强停住。他来不及把手收回来,扭过头看见车门边站着一个身形细瘦的青年男人,瞪大了眼睛看着他,眉骨高挺眼窝深遂,是一副似乎有白种人血统的混血儿的长相。
关逾明冷冷地看着他,依然保持着原先的姿势,两个人相对无言,气氛凝固在了尴尬的节点。
“小六!你没下车啊!幸好我们没走,”俞幼清从青年人身后探出脑袋扒着车门往里看,冲着关逾明包含歉意地笑了笑,“要是把你锁在车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说怎么办?哎,我刚叫你你怎么没下车呢?是不是那会儿我吵你没睡好?不要紧,我跟你说这儿的蒙古包里可舒服呢!就那床躺着比你家里那木头板子强……”
“师叔,”关逾明微微皱起眉头,叫了他一声,打断了他很快就要奔涌而出而且已经可以想象到会滔滔不绝的话,“行李都堆着,我出不去。”
“没事没事,我这就把东西都搬下来,”青年人趁着这个机会插进了话茬,回过头对俞幼清笑着说道,“小兄弟,你往那边站一站,我把你们的行李搬下来,让你这个朋友先下车。”
“嗨!哥,叫我小俞就行,这个不麻烦你,”俞幼清说着,伸手拽住一只好大的箱子轻而易举地拖出车门外稳稳当当地放在了地上,“我们这些东西也不多,大部分都是思昭跟陈彻采风用的器材,”他把另一只大箱子拽出来放在地上,“当然也有不少是我带来的,我这人特别不会收拾行李,带东西总带一大堆,最后也不知道有用没用,要不是每回出远门都有阿景帮我收拾,我跟你说,我肯定得带着俩箱子不止。”
“我总能听思昭提起你们,”青年人笑意盈盈地帮着俞幼清把箱子抬下来,抬起头看了关逾明一眼,“听说你们是他剧场里的常客。”
“嗨!我们俩就是喝酒认识的,再说都是干剧场工作的,多少算半个同行,互相了解一下行业发展,交流交流经验,”俞幼清大大咧咧地往箱子上一坐,抹了一把脸上的汗,冲关逾明招招手,“行嘞,六子,下来吧。这回是师叔对不起你啊,赶明儿回去请你吃京天红。”
关逾明点点头,没戳穿他自己想吃京天红炸糕的心思,放下手里的棒球棍灵巧地从缝隙里钻出来,跳出车门,回过身默默地拽住两只箱子提出车外。
“你也是做演员的吗?是演话剧吗?还是舞台剧?”关逾明探身去拽另一只箱子的时候,听见那个一身宝蓝色蒙古袍身形瘦长的青年问道。“我?我哪儿演得了话剧,我二师哥老说,就我这个嘴,死人都说活了,多少搞殡葬业务的都得恨死我,这要是上台演话剧,一页的台词儿我能说出三页来,”俞幼清站起来接过关逾明手里的箱子放在地上,顺手从他的衣兜里摸出一只布袋拿在手里抛来抛去,关逾明回过头,分明看见他冲着那个青年露出一个十分狡黠的笑容,关逾明认识他的年头太久,顿时明白他心里想着逗趣,可是又不好拆穿他,只好把搬下来的行李挪到更空旷些的地方,“我是个相声演员,我们俩都是。”
他指了指自己又指向关逾明,从红丝绒的布袋里摸出两块竹板在青年眼前一晃,两手攥住打了个花点儿,响声清脆透亮,十分悦耳动听。青年人似乎是愣了一下,然后很快就了然地点点头,说:“我知道,在北京两个人表演,舞台上还要放一张桌子,对不对?”
“对对对,我们俩都是表演那个的,哎,哥,你听过相声没有?”
“听过几次,”青年人点点头,抓住蒙古袍的腰带紧了紧,“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寝室的冯昔是北京本地人,他说自己是四九城里长大的北京土著,所以总带着我们寝室里的同学一块儿玩,他自己喜欢听相声,就拉着我们都去,美其名曰帮我提高汉语水平,那时候我汉语说的很不好,他第一次带着我们去的时候,我一共也没听懂几句,”青年人笑着揉了揉后脑的头发,“别人鼓掌我就跟着鼓掌,也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后来又去过几次,汉语也变好了,还是能听懂一些话的。”
“听相声提高汉语水平?哎哟,那您这起点可不低,”俞幼清笑嘻嘻地说道,回手拽住关逾明的后脖领子把他扯到自己身边勾住肩膀,指了指对面的青年,“六子,这是思昭的同寝舍友,斯钦布赫大哥,是正儿八经的歌剧演员,咱这几天就要多叨扰人家了,哥,这是我小师侄关逾明,他在师兄弟里边儿行六,我们那儿都管他叫小六,您也叫他小六就行。”
“关逾明?很高兴认识你,我叫斯钦布赫,是这里长大的蒙古族,欢迎你来草原。”蒙古青年斯钦布赫微笑着向关逾明伸出手,阳光下他的手指修长漂亮,和他脸庞一样泛着浅蜜色的光泽,关逾明礼貌地勾起唇角,轻轻握住他的手微微颔首。
“您好,我叫关逾明,这几天要叨扰您了。”
“这是哪儿的话,”斯钦布赫笑着摇摇头,轻轻收回手,“我这些日子一直住在家里,人没在北京,思昭和我打电话的时候总念叨他新认识了这些朋友,思昭人特别好,但他可不是那么容易和人交朋友的人,这还是他头一回带朋友来我家呢,一会儿吃过饭,我带你们看马去。”
“真的?哥,我能骑马不?”
听到有看马的机会,俞幼清的眼睛登时像装了灯泡一样亮起来,斯钦布赫被他的神情逗笑,好半天才止住,浅蜜色的脸颊上上浮起一层浅红,他轻轻喘着气,笑着弯腰去拿剩下的行李箱,关逾明也伸手过去帮忙,三个人很快就把东西都搬了出来,刚才去了洗手间的几个人也折返回来,一行人搬着行李箱爬上草坡,来到一片蒙古包前。
“每顶蒙古包能住两个人,这两顶我已经收拾好了,你们没过来的时候我住这里,”斯钦布赫指了指眼前最近的一个蒙古包有些抱歉似的说道,“原本门图要过来帮我再搭一顶,但是他临时有事没来,牧区的人家都离得太远,我一时没找到人,单独住的朋友今晚就先睡这里吧,真是太对不住了。”
“别啊,老大,”宋思昭连忙摇头,“你可别再去和巴雅尔挤了,他哪天能跑了喝酒?要不今晚咱仨挤一宿吧。”
“布赫,别过去了,夜里骑马不安全,”宋思昭的另一个室友陈彻下颌上蓄着一撮微微卷曲的小胡子,整个人散发着艺术性的气息,“以前在寝室咱也不是没俩人挤过一张没一米宽的床。”
关逾明料想到,俞幼清是一定要跟景行睡一顶蒙古包的,他这人睡相极不好,除了景行谁也受不了他,小时候跟关逾明一块儿睡,总得抢了被子把他踢下床,宋思昭和陈彻是同寝舍友又是相识快十年的老同学,和关逾明一共也没有见过几次面,互相之间最多称得上点头之交,肯定不会单独挑出一个人来跟关逾明住一顶蒙古包,一来二去落单的想必就是他自己,于是沉默地站在一旁听他们说完了话,趁着斯钦布赫犹豫的片刻,轻声说道:“布赫大哥,如果您不介意,就委屈您和我挤一晚吧,我睡觉时还算老实,不常乱动。”
认真看向斯钦布赫的时候,关逾明才发现斯钦布赫比他稍微矮着几厘米,蒙古袍里的身躯纤瘦劲韧,不像一般的蒙古人那样健壮,关逾明虽然从小就细瘦,骨架却还是比他大了一圈,顿时有些畏缩,不着痕迹地往旁边挪了挪,拉开两个人的距离。自从十三岁那年开始不停地长个子以后,关逾明就很少再和别人站得很近,他从小身姿挺拔,不驼背也不弯腰,同龄人都比他要矮一些,站得太近说话时就没办法平视,他总还是更习惯看着别人的眼睛。
斯钦布赫大约是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愣了一下,似乎还是有些犹豫不定,关逾明想了想,又补充道:“我一个人住蒙古包,恐怕不习惯,而且,不怕您笑话,我从小就胆子小,到这样的环境里身边没有人,实在是害怕。”
“没事没事,你别担心,也别害怕”斯钦布赫蹙起眉头连忙摆手,关切地看着他,抬手拍了拍他的背,“现在草原上狼已经很少了,现在这个季节不会有狼到牧区来的。我不介意的,只要你能习惯,那今晚我跟你先睡这一顶,等明天门图回来,搭一顶新的。”
一行人整理好行李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夕阳贴近了远处青蓝色的地平线,橙红颜色晕染了大半的天空,慢慢褪成柔嫩的浅粉,最后融入淡淡的蓝天。离吃晚饭还有一会儿,俞幼清挽起袖子拉上景行帮宋思昭洗菜,关逾明不知道自己应该做点儿什么,在蒙古包前来来回回转悠了半天,正巧斯钦布赫从屋里端出一筐水果,看他有些无措似的,便把筐递给他。关逾明心领神会,到取水的地方提了一桶清水,蹲在河边仔细地洗水果。这条蜿蜒的小河距离他们住的蒙古包并不远,蹲在河边能看见蒙古包门口忙碌的几个人。关逾明洗干净框里的葡萄,掬起一捧河水洗了洗手,抬起头看见陈彻扛着很大的一台机器朝着远处走去,背上还背着不小的背包。
他听说陈彻毕业以后没有继续从事歌剧,而是转行做了摄影师,在北京一家风格和理念都很前卫新潮的工作室做专职摄影师。这一次他到内蒙来是为了采风,这会儿大约是去取景了。陈彻供职的工作室“WAVES”关逾明很熟悉,老板齐野是他好多年的朋友,两个人因为父辈的交情从小相识,但是因为齐野一直在国外读书,两个人直到齐野回国定居才熟络起来,性子爱好虽然都截然不同,但是他们两个在一处总不会无趣。“WAVES”在北京扎根的第一套作品是以老北京风貌为主题的系列片,当时关逾明还友情客串了一次模特,大半时间用背影出镜,只在最后一张照片里留下了半张模糊的正脸。那套片子后来参加了展览,广受好评,齐野和他的工作室由此在京城站住了脚跟,逐年壮大。陈彻入职不过是最近一年的事情,关逾明也是偶然间听他谈起才知道这么一回事,他和齐野也总没见面,偶尔电话联系,往往也是齐野在电话那头说着,他举着手机默默地听。北京城太大,想要碰见熟人何止难上加难。
关逾明正仔细揉搓手里的苹果,背后忽然响起脚步声,他回头一看,俞幼清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一身褐色的蒙古袍踩着黑色的靴子大踏步地走过来,大咧咧地蹲在他旁边。
“师叔。”
“哎,六子,你看我,帅不帅?”俞幼清扯着身上的袍子笑得十分灿烂,两排牙齿闪着晶莹的光芒。
“嗯,”关逾明点点头,盛了一瓢水继续揉搓下一只苹果,“帅。”
“哎呀,看看你这个敷衍的态度,这衣服人人有份儿,一会儿你回去也试试,”俞幼清听完他一个字都不肯多的话连连咋舌,盘腿坐了下来,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你跟布赫大哥挤一顶蒙古包?那是一个人住的,可就一张床,你跟我睡都睡不着,跟刚见面的人睡一张床?能踏实吗?”
“如果布赫大哥不留下,夜里他还要骑马赶路,”关逾明把第二只干净的苹果放进筐里,拣出了第三只,“来者是客,没有让主人家离开的道理。只睡一晚上,也没有几个小时。”
“委屈你将就一晚上吧,我现在有点儿后悔拽上你来这儿了,”俞幼清长叹了一口气,在柔软的草地上躺下来,两手交叠枕在脑后,关逾明感到很意外,扭过头看见他正盯着渐暗的天色出神,嘴里小声地咕哝着,“本来吧……我想着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解老三那个小兔崽子是跑出国了,许诚梧呆在北京里哪儿都没去,就弄得你两头不是人,我琢磨着拎你出来散散心,放你一个人走谁也不踏实,哪知道攒这么个局宋思昭也能忘了告诉人家具体人数,我就说这孙子办事儿不地道,除了喝酒,嘛事儿没用。”
关逾明微微笑了一下,埋头继续揉搓苹果,轻声说道:“布赫大哥人挺好的,我总觉着他有点儿面熟。我没事,师叔别担心。”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没准儿,”俞幼清翘起左腿把右腿搭上去,老神在在地晃悠着,“平常齐野不是总约你听音乐会看歌剧嘛,可能哪回你听过他主演的歌剧吧。再说他长得那么好看,就算再看不清楚人脸,也能有点儿印象。”
“没准儿。”
“哎,老三要是不回来了,你往后怎么办?再找个搭子?还是说单口?我觉着你说单口……就这个一脸的礼义廉耻仁义道德,包袱够呛能响。”
“我跟解珩没裂,”关逾明把剩下的水果都洗干净,用最后一点水过了一遍,“暂时先单着吧,后台谁需要,我就捧一场。震哥最近忙着签售,大师哥落单的时候多些,师父让我先给他量活。”
“解老三那小子没个一年半载可回不来,他你还不知道嘛,”俞幼清灵巧地翻身坐起来拽平衣襟上细小的褶皱,“别看一天到晚那股狠劲儿跟什么似的,心里嫩得赛着豆腐,霍震再忙他那搭档也不能让给你啊,你怎么办?就成下岗青年啦?”
“大师哥预备着把店面翻修一遍,他得带孩子,没多少空闲时间,我帮他盯着,算他雇我,”关逾明端着筐站起来,轻轻绷直双腿舒展开酸痛的肌肉,“再不济,我就上石景山画扇子骗游客去,怎么都是工作。”
“去你的,”俞幼清站起来,拎起水桶,用手肘推了他一下,“这么多年你那画扇子骗游客的心思还没变?真以为人家都人傻钱多呢?再说景区里能有几个识货的,你画的扇面怎么说也值个千八百块钱,三十五十的一把就卖了,多亏得慌。”
“画是人画的,有人买就行,挣口饭吃足够了。”
“滚蛋滚蛋,你个丧良心的小兔崽子,一天到晚胸无大志,光卖扇面行吗?你还得买点儿卷轴写两幅字放在那儿卖,这样显着档次高,好提价,知道了吗,小兔崽子?你可太不会做生意了!”
关逾明看着他洋洋自得像只花孔雀似的样子,想笑又觉得不好,抿住了嘴角把笑意憋回去,点点头,闷声说道:“好,我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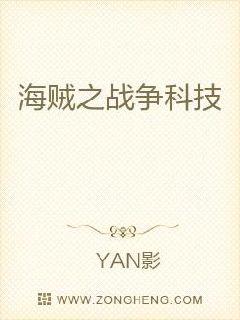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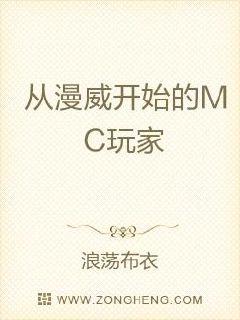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