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黄小姐》最新免费章节夏之章第七章
夏之章第七章
我家离上海的距离,在地图上看也就是弯弯曲曲的一条小毛虫,但我要行走到那里,可就是西天取经的的艰难长路。我走了十天半个月,还是二十多天,我也忘了,况且我还带上了黄静,走的很累,纳的鞋底都磨成了硬面皮。
我把孩子给了母亲 ,母亲来回拉锯了好久,才愿意带孩子。我一开始不想带孩子去的,但最后还是带上的,因为母亲说好有个伴,其实她是想少一个负担。
为什么带黄静,这个是天注定的,因为我是用抓阄的方法来选择的,不然孩子都想跟我去‘闯世界’,看看外面的花花草草。
三女儿黄静和我很像,无论外表还是品性。
我找到了屈先生住的地方,但是他搬家了,辗转了很久,我才得知他当时新的住址。
我敲门,屈先生开了门,他吓了一大跳,又看了看长得快认不出来的三女儿,又再次吓了一激灵。
“屈先生!”我幽幽的从嘴里吐了出来,眼眶红了起来。我太累了,快走不动了,受够的行走的生活,像是摇曳在空中的枯叶子,悠悠荡荡。如果让日子倒回去的话,我一定……不来上海,即使前面是荣华富贵……我也不会来。
我并没有说我太累了,憋在心里的话,就是想要骂人的脏话,我想要骂人,但是脱口而出的是:“屈先生,我想你了!”
我梨花带雨的拉着黄静的手,看着屈先生的眼睛。
我们跟着屈先生走进了小而干净屋子。
我们坐在床上,看着屈先生忙来忙去的给我准备喝的茶水和吃的东西,我就是盯着他看,他白了,比我还白,我知道,他这是捂白的。
我和黄静当时的喝像和吃像,我至今不想形容,这完全不是我这个黄小姐该有的动作,这是人的天性,原始的天性使然。
我和屈先生交谈的很久才知,他搬家了,前段时间没寄钱是因为去了趟医院,似乎是心脏有问题,钱都买了药,救心丸时刻备在衣兜中,以防万一。
我很郁闷,屈先生好旱烟,若是得了肺病我还好理解,他得的是心脏病,这有点牵强。好比天天在河里游泳的人不是淹死而是被火烧死。
我和黄静住下了,一住又是三年。
屈先生得了个铁饭碗,政府的,给一个小军官倒尿罐,我没有说笑,是真的倒尿罐,早上端着尿罐去拉路上专门拉屎牛的车上渠道。
我也谋得了一份工作,和他在一起,给小军官沏茶。每次躺在床上想到这事,就想要笑,因为我和屈先生承上启下的把小军官给打通了。
我们有了上海户口,我每个月三十块钱,他每个月六十块钱,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大钱,并且我们住的房子也成了自己的房子,我还在房子钱开垦出一片园地,种的蔬菜花果可勉强够吃。我每个月寄钱回去,母亲也没有抱怨,有三个可以帮助干活的孩子,她何乐而为之。这是我黄家被打倒后,迄今为止最为繁盛的境况,我似活在云里雾里。
黄静越发随我,像我小时候那般清冷、傲气。她在上海上了学,遗传了我的脑子,学习很好。老师每每来我家都会说:“侬闺女脑子好的很伐啦。聪明的很那!”
我也学着上海的咿咿呀呀的口音回道:“侬教的好的很的!”
老师很会夸人,嘴上像是涂蜂蜜一样,我也不例外,也把她说的很开心。
我很幸福,在这个时间段里。
屈先生还是一直抽旱烟,从烟袋里,捏出些许烟丝,往烟锅里塞呀塞,顿呀顿,划了个洋火柴就抽了起来。那天他也如此点烟、压烟丝、抽烟,不知道哪一个环节出现的错误,那个烟锅里的丝丝火星就把小军官家的厨房给点了,星火和燎原的事实,不是凭空捏造。我说过的旱烟会害了屈先生,我想说是害了他的身体,但此时却把他的工作给害了。照着我二哥的面子,小军官家并没有责罚我家的屈先生。真巧遇到了哪个年代职工人员精简下乡,我家就从上海精简到浙江,从浙江精简到杏镇,户口从上海迁到浙江,从浙江又迁回了杏镇。
我们又回去了,回去我们熟悉的地方。
我想那个小军官对屈先生把他家房子点了,还是有怨恨的,虽然报复在很久之后。
我在上海的房子没了,我开垦的园地也没了。黄静不愿意回老家,她过惯了城里的生活,对于镇中的日子,估计需要好长时间才能吃得消。
以前的我遇到这种事不会怪罪屈先生,可是伴随着年纪和阅历,我非常的怪罪屈先生,他把我的好日子给毁了。他则非常不以为然,淡淡的说:“正遂了我的意,可以回去和孩子团圆了。”
屈先生成了精简下乡的人,工资降了不是一点,而是很多,他的收入根本养活不了我们,况且他还要吃救心丸,还要抽烟。
屈先生抽烟越发的凶了起来。我总是呵斥他,但他并不听我的,也不和我说话,这和我们才结婚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我们回杏镇没有多少日子,就听见了关于母亲的很多闲言碎语。
母亲和屈大伯有一腿,我不管它真与否,直接就去找母亲来问了究竟。我得到的答案是‘真’。
母亲坐在木凳子上,我站在她面前急赤白咧的嗷嗷直叫,喊了半天,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有说出来。我堵在内心的无可奈何的唏嘘之情,不知如何抒发给我眼前保养的很好的黑发母亲,我笑了起来,夹杂着苦涩。我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想唯有母亲突然离去,这才能消除我芝麻大小的羞耻。
我一圈一圈走着包围着她,我希望走下的脚印可以瞬间塌陷,把母亲没在圈子里,别再出来让人家说闲话。我在母亲面前情感宣泄的天轰地裂,以为她早就被全镇的人疏远和唾弃了,可是并没有,镇上的人对她如故,母亲以为她和屈大伯做的保密工作很好,谁都不知道,其实不然,只是大家瞒着你,让你以为被人不知道,但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奇怪的处事之法。
人世间相处之法就是如此,即便关系甚好的俩人,都会瞒着你一些事情,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你不知,但围在你身边的人全知的事。屈大伯、我母亲、屈大嫂不知道,杏镇其他的人全都知道,所以说圈里不知道圈外,圈外的人早就了解所有圈里之事。
母亲把前因后果交代一遍后说:“我们眉来眼去的日子比较长,但真事就一回,也不能全责怪我,你家屈大伯常来溜达,给孩子们带些吃的,其实他挺好的,这么疼爱你家孩子。”
我瞪大了双眼,甚是意外。
母亲:“眼睁那么大干嘛?”
我说:“我在家那时,过的很不好,他可从未来过我家!”
母亲不说话。
“真是爱屋及乌!”我又说。
我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之道。我问屈先生该如何,他回道:“都已经发生了,是历史了,只要从现在切断,就没有以后。”
我瞧着屈先生,他这哲学思想也不知跟谁学的,让我对他有一丝敬佩。
在回到杏镇之前,我和屈先生从上海转到浙江,在浙江的一个乡镇住了约莫半年,我不知道屈先生当时的想法,他也没有和我说,就把转到浙江的户口给卖了,卖了多少钱他也没有说,就说是卖了,最后我们的户口又转回了杏镇。知这件事情的最后结果的时候,我和他大闹了八百回合,手脚并用,最后还是打道回府。
才回去的那几天过的还算开心,之芯、之莱和之易这三小‘之’用的好长时间才把他们的父亲熟悉起来。
之芯和十岁的之莱抱回来一个很大的西瓜,不知道从那家田里偷的。我就问,之芯走到我旁边对着我耳朵回道:“小辫叔叔从他家地里偷偷摘给我们,让我送回来给你和爹吃一吃,西瓜很甜,他说不要张扬!”
我把西瓜放在从井里才打出来的冰凉的水中,冰镇到了傍晚。
暮色渐浓。
我们搬出来一张床放在院子里乘凉,四个孩子并排坐在床沿边,我和屈先生坐在床边的小凳子上,开心的开始吃起西瓜来。我们一直往外吐西瓜子,‘噼里啪啦’的连着我们自己的口水吐了出来。我家的之易突然开发出一个好玩的吐子技巧,我想这是基于他已经吃饱西瓜的基础上才想出的打发时间的游戏。他用劲把嘴里的西瓜子往远处吐去,然后问之芯:“你能不能吐的比我远?”
之芯骨气嘴巴‘噼里啪啦’的往远处吐了好几粒。
我们似乎都觉得有趣,全部铆足劲,把西瓜子储存在嘴里,然后往远处吐去。
我们嘻嘻哈哈的吐着吃着,伴随着西瓜子落地的清脆的声音很是愉悦,这个时候,我家园门的墙角突然冒出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头,在快要沉下去的暮色中显得很是瘆人。
屈大伯从墙角渐渐的现身,说:“吃西瓜呢?”
我们一家六口人瞬间失声,没有想好如何回应,之芯满嘴正准备往外吐的西瓜子,吓得都顺着嘴巴掉了下来。
屈大伯:“你回来了?”
屈先生点头道:“回来了!”
我问:“你可有事?”
“没事,就是刚从西瓜地回来,这两天西瓜地不太平安。我就路过这,早知道摘一个西瓜给你家了!”
我回道:“谢谢!已经……有了。”
屈大伯:“我没事,我先走了!”
屈大伯走后,我们松下心来。
他家那年种的西瓜似乎都变成了我们杏镇公共解暑圣地,那种不用花钱的。虽然他家也用了很多方法去保护,但似乎没有多大用处,除非你一直都去看守,不然总会被人逮着时机下手。最后似乎杏镇上的人做的太过分,屈大伯只好把床搬到地头前,吃饭睡觉都在那里。
第二年,屈大伯再也不敢种西瓜了。杏镇的父老乡亲们从他家身上也得到了教训,从不种西瓜,这让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少了很多乐趣。
那天的西瓜真的很大,之芯和之莱俩人合力抱回来的。我们六个人把一个大西瓜全部吃到肚子里后,很是满足。晚上我们比平时起床的次数多了很多,围绕我们的蚊子也多了许多,似乎它们能够闻到我们血液中的西瓜甜味,那夜它们对我们猛烈的攻击着,我一夜没睡好,跪在床上就这月光,伸手去拍打蚊子,‘噼里啪啦’一晚上。
早上醒来脸上、腿上、胳膊上全是斑斑红点,红的颜色跟西瓜红一般模样,白色的蚊帐上残留着蚊子黑色的被我碾碎的夹杂着血迹的残体,我手上也是如此,我想这就是偷吃别人家西瓜的惩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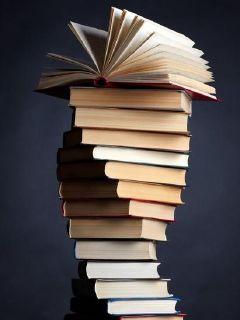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