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岁月》最新免费章节第一篇青阳晨霜第五章大年夜
第一篇 青阳晨霜 第五章 大年夜
五柱妈跟二顺娘说担心金柱狗样别叫小妖精逮着,可她自己确喜好跟男人们打情骂俏嬉闹耍笑。那回,花花看见五柱妈跟裁缝赵悦景嬉闹的场景,就是五柱妈当着裁剪制作衣裳客人的面,把赵悦景那张白皮脸按在自己温热怀间的。
那日,又是花花跑去裁缝铺子闹着五柱妈要吮乳水,赵悦景本来在裁缝案板子前活儿干的好好的,听到花花要五柱妈给她吮乳水,立马上了巫神似的,贼眉鼠眼地盯着五柱妈鼓起的双胸,又瞅着花花猥言:“花花,快吮吧,稀甜稀甜的呢,不吮叔叔可要吮喽。”五柱妈听了这话也怪心痒,那几日正愁着无钱去国营粮站买回供应的玉米面儿,于是,五柱妈藏着心思推开了花花,一把拽过赵悦景衣领,两人当着制作衣裳客人的面就疯闹了起来,这个掏那个一下,那个摸这个一把的,两人嘴里还嘻嘻哈哈地怪说怪笑着。
两人疯闹间,也不知是赵悦景的故意还是五柱妈的有意,几个回合过去,五柱妈就将赵悦景那个白皮脸按在了自己胸间,口中大笑道:“俺五个儿子都吮过,哪里还缺了你一个咧!尝尝是稀甜稀甜的不是?……”赵悦景被五柱妈弄得两手一抹,白皮脸顿时变成了戏台子上的曹阿瞒,连那个制作衣裳客人都笑得肚子岔了气。
这时的五柱妈,仿佛感到的竟然是异常的淋漓畅快舒心满意,佯装大笑着,一手抹着赵悦景白皮脸,一手趁势从赵悦景裤兜里掏出一张钱票攥在手里。
五柱妈此时方感心情十分的大好,但没等五柱妈畅快到心花怒放,就招来五柱爹的一顿暴打。
傍晚,五柱妈一进家门,五柱爹立马把五柱妈按到在黄油漆过的土炕上,三把两把撕光了五柱妈的衣裳,一双老茧大手左右抡起,大巴掌打得五柱妈满炕乱滚,仰面打五柱妈的腹,背面打五柱妈的臀,打的五柱妈野狼哀嚎般地喊叫着,吓得柱柱花花躲在一旁瑟瑟发抖。五柱爹从未如此地暴打过五柱妈。
五柱爹打五柱妈本来就是他俩生活中一项很平常的内容,如同隔三天五日衣裳脏了就得脱下再换上一件那样。五柱爹一段时间不打五柱妈一回,五柱妈仿佛浑身就觉得不十分自在似的,好像做菜时忘了放五香粉甚至是咸盐,按照五柱妈的说法,那叫皮子又痒痒了呢,于是便寻衅着五柱爹能够打她几下。
五柱爹从不在外人甚至是孩子面前打五柱妈一下,比划着要打的架势都没有过,数落埋怨当然也是没有的,不论五柱妈是不是什么事做错了,还是什么事丢了丈夫的面子。在五柱妈面前,五柱爹犹如五柱妈的最大的儿子似的,就连五柱爹为丢弃银柱而遭受五柱妈狠狠地咬了一口,几乎那块胳膊肉差点儿都被咬掉,五柱爹连半个不字都没吭一声,事情过后,一切照旧。这使五柱妈十分得意,并引以为豪地在坝岗街上能够对别的女人说三道四。坝岗街人都以为老五柱家是皇权制,其实皇权之上还有个后宫娘娘,只不过,后宫娘娘不理朝政罢了。
五柱爹尽管大字不识一箩筐,但在他的生活里,俨然是儒家的忠实弟子,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德而行为要旨,夫妻而人伦之首。当然,五柱爹是严格遵循着祖上留下的当面教子背后教妻的训导。常常,五柱妈在挨完一两下打之后,五柱爹一定会在夜里变得无限温存似一只绵羊羔子一般,五柱妈也一定会骄傲地像一只母鸡,调头摆腚地逗引得五柱爹围着她心急火燎地团团乱转,这大概就是五柱妈每每情愿挨打的缘故罢。
其实,以往五柱爹对五柱妈的出手大抵都是相当有分寸的,譬如:起掌看是重,落掌却是轻,老茧大手看似狠狠地拎过来,到皮肉上却只是摸摸索索,实质是挠痒痒一般的效果。五柱爹和五柱妈的这种打和被打,仿佛是一种别样的前戏,宛如常人的那种恩爱和亲昵,似乎那样才是充盈着那个时代夫妻间的爱慕之情。
这次五柱妈因赵悦景挨打,是五柱爹对儒家弟子的一次背叛,因为这是一次实实在在大打出手般的真打,是五柱妈嫁给五柱爹十几年仅有的一次真打,五柱妈不由地有些过度伤心。
在五柱妈被打的同时,因事出裁缝赵悦景,五柱爹又不免提到银柱的种源问题。五柱爹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五柱妈立身站起,胸脯一挺,严词以对,毫不含糊地一口咬定:“银柱就是你的种,而不是你说的什么赵种悦种景种的种,祖宗在上,良心在这,我敢对天发誓,银柱若不是你的种,一个霹雳天雷炸死我!”
五柱妈大字不识几个,根本不懂得去医院检验血型之类的科学,唯一能出言为证的就是银柱的一双类似老鼠的小眼睛和一盘国字型的脸,跟五柱爹的简直就是一个模子磕出来的。那时,五柱爹根本认为五柱妈这些全都是鬼话。
五柱妈当然没有忌讳是花花向五柱爹告的状,自己的孩子自己生的养的咋样都行,这是五柱妈为妻做母的基本原则。在五柱妈心里,自己的六个孩子都是娇娇嫩嫩的小花骨朵,自己就是生养了六只小狗崽子的母狗,折了哪支小花骨朵她都伤心,碰了哪只小狗崽子她都心疼,当然也包括她的二子银柱。
五柱妈算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被五柱爹痛打的第二天再去赵悦景裁缝铺子缝制小布块儿时,五柱妈故意弄得两眼红红眼泪汪汪的样子,显示着是因为赵悦景而受了委屈白白挨了一顿好揍呢。
五柱妈在向赵悦景哭诉着自己冤情的时候,还掀起前腹后腰叫赵悦景看看这儿也让赵悦景摸摸那儿的,身上累累伤痕,脸上泪水涟涟,五柱妈对赵悦景说,这些都是为了他而落下的,弄的赵悦景非要给五柱妈两块钱作为补偿不可。
五柱妈假意地推让着那两块钱,说:“就是你这心里,还知道心疼着人家的呢。”赵悦景死活地把两块钱塞进五柱妈手里,嘿嘿地笑着说:“俺这不也是心疼着一朵好花插在牛粪上了嘛。”
五柱妈一听这话,立马就不干了,拉耷着脸对赵悦景说:“说谁是好花?说谁是牛粪?我看,来福妈是好花,你就是那粕稀溜溜臭烘烘的牛粪呢!赵裁缝,俺可是告诉你啦,俺家五柱子他爹那可是一等一的汉子,你这样的呀,十个八个捆在一起,怕也是比不了的呢!”
赵悦景听了五柱妈这话,觉得一派的莫名其妙,明明是自己挨了一顿好揍,别人爱慕怜悯而帮腔数落着,她反倒责怪别人数落着揍她的人,这女人的心思呀,还真叫人琢磨不透呢。
五柱妈的两块钱,一块钱拿去国营粮站买回八斤玉米面儿,一块钱给五柱爹从五道桥副食品店买来半斤地瓜烧老酒半斤熟猪头肉。五柱爹哪里舍得自己吞下那馋人的熟猪头肉,吃晚饭的时候,五柱爹把熟猪头肉一分两半,搁在花花跟前一半,搁在柱柱跟前一半,柱柱小眼睛死死地盯着,花花伸出筷子就要夹,五柱爹“哎——”地一声,花花赶紧缩了回来,五柱爹伸出筷子,从花花那份里夹出一片搁在栓柱碗里,又夹出一片搁在锁柱碗里,然后,从柱柱那份里夹出两片搁在五柱妈碗里,筷子在自己嘴里一呡,大声说:“开饭啦。”说完,端起酒碗一口喝个净光,夹起桌上的咸萝卜干儿,咔哧咔哧地大嚼着。五柱妈赶紧从自己碗里夹出那两片熟猪头肉搁在五柱爹碗里,对五柱爹说:“快吃啦,谁不稀罕那东西,油油腻腻的。”柱柱瞅着五柱爹,花花瞅着五柱妈,五柱爹说:“俩小东西还瞅什么,吃饭。”五柱妈眼里一滴泪掉在碗里,金柱银柱都看见了,五柱妈赶紧连饭带泪吃进了肚里。
夜里,五柱爹酒劲散去,兴头儿悠上,搂着五柱妈直啃直咬,五柱妈仍然嘻嘻乐叫不止。那夜,俩人撕闹间,五柱爹低语地问五柱妈:“打痛了你吧?” 五柱妈嘻嘻一笑说:“喝足了猫尿儿不是?” 五柱爹呵呵地笑着说:“老长时间没喝到这么纯正的地瓜烧老酒咧,你还真是舍得呢。”五柱妈按着五柱爹的鼻子头,嘻嘻笑着说:“一喝猫尿儿就上来神儿啦,赶明儿,看哪个不识好歹的还买给你才怪呢。”五柱爹还是嘻嘻笑着说:“就是你这个不识好歹的呗。”五柱妈一听就火了,拽着五柱爹的一只耳朵说道:“哪个是不识好歹的?”
五柱爹搂着娇小的五柱妈商量着说:“咱别去缝制小布块儿了,好不?” 五柱妈一听,立马说道:“这事,眼下跟你没个商量,等金柱有了工作再说吧。”五柱爹听了,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更是把五柱妈搂得死紧死紧的了。
后来,是五柱爹细数了一数,花花上小学一年级之前是一直吮着五柱妈乳水的,五柱爹说花花不吮乳水,家中便又得添口,五柱爹再也承受不了继续加重的负荷呀。
不久,学校放了冬假,五柱爹叫银柱也跟着金柱去帽盔山砍柴拿街上卖钱。帽盔山离坝岗街有十多里远,天又寒冷得邪虎,银柱显露着不愿去的情绪,被五柱爹斜眼瞄见,一个老茧巴掌搧在银柱脸腮上,银柱小脸登时鼓起五道血痕。
五柱爹冲着银柱吼道:“过去没念书的时候,叫去干嘛就去干嘛,不是也砍过柴嘛,今番念书了,是要做举人秀才啦,就不能砍柴了是不?是嫌丢人现眼还是怕吃苦出力呀……。”
银柱挨了五柱爹的打又挨了五柱爹的骂,心里暗暗记恨。但银柱却没哭,银柱打小就从不因挨五柱爹的老茧巴掌而去哭,总是用一双小鼠眼直勾勾地瞅着五柱妈,心里企盼着能够得到五柱妈的爱怜,却不料,这时的五柱妈仍然在一旁加盐添醋,也在大声地冲着银柱吼:“活该!都十好几的汉子啦,怎地不学着出去赚点儿钱!你爹打你就对啦。”自此,银柱对五柱妈更是增添了更多的失望和嫉恨。
坝岗街人都说,老五柱家的五个柱子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跟他爹一样的死犟驴子。
银柱被五柱爹的老茧巴掌搧肿了脸腮,晚饭也没吃,一赌气出了家门,都大半夜了也不见银柱回来。
五柱妈叫金柱裹着五柱爹的破皮袄,在坝岗街从北到南地寻找,三大胡同也都找了个遍,又在安东大街小巷寻了大半宿,终不见银柱身影,金柱冻得哆哆嗦嗦,回到家里哮喘大发。
五柱妈见五柱爹依旧在黄油漆过的土炕上爆发着响彻如雷的大鼾,便悄悄地下了炕,从盛着小半罐白糖的罐子里舀出半勺白糖,用暖瓶里的热水冲了,递给了金柱说:“赶紧喝了,别叫你爹看着。”
那夜,银柱一人端端地坐在帽盔山顶立陡的仄石崖上,饥肠饱饮隆冬寒风,弱骨强挨漫山冰雪,银柱对五柱妈的失望和嫉恨演变成了少有的绝望。银柱想就此从这方立陡的仄石崖上飞身跃下,也好为五柱爹省下一碗玉米面儿糊糊。
那年冬日,数九寒天,北风煞骨,冰雪封山,大冷至极,坝岗街上冻得连个人影也没有,金叔家的大黑狗都被金天虎放进了外屋地暖着怕冻坏了。
天寒地冻,不能上山砍柴,金柱便窝在屋里辅导栓柱数学,锁柱不用辅导,金柱便只对栓柱一个人教授。
那边的银柱,一手倒背,一手持书,端步轻迈,摇头晃脑,慢条斯理,字腔圆正,学究一般,一字一板地朗诵着他最喜欢那篇课文《崂山道士》: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崂山多仙人,负笈往游,登一顶,观有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团上,素发垂领,而神观爽迈,叩而与语,理甚玄妙,请师之……。
银柱嘴里朗诵着,脑袋却冷丁想起,前天夜里从七道沟里电力变压器工厂围墙翻出来时,看见李秀芳老师为什么会跟一个男人搂抱在一起。那夜确实天寒地冻般的极冷,电力变压器工厂的那条大黄狗也都冻得瑟瑟发毛,卧在背风的墙角,狗嘴埋在狗腚里明知银柱翻墙进进出出也不咬不叫的。
这天,五柱爹冻得浑身上下哆哆嗦嗦,是刚刚落日就回到坝岗街这间低矮破旧窑子房的。五柱爹身子散着阵阵寒气,鼻头冻得通红,麻脸也有些红肿发胀,进屋半天狗皮帽子都没摘破皮袄也没脱。
五柱爹一眼瞄见金柱正在煞费心机地为栓柱教授讲学,银柱在哪儿端着课本咿咿呀呀地摇头晃脑,顿时火冒三丈,飞起一脚,将小方桌立刻踢翻,书笔洒落在地,口中骂道:“狗他娘的!肚皮都添不满,也不去上山砍柴,倒有闲心弄这卖腚玩艺! ”
金柱叫五柱爹这一脚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发抖,银柱自知没去砍柴理亏三分大气也不敢喘,默默地蹲在地上帮着栓柱拾书捡笔。
这时的五柱爹瞅见银柱瘦瘦细细白白净净的模样,立马又想到了同街裁缝赵悦景的那张白皮脸。于是,五柱爹心中的憋气顿时演变成眼里冒火。 那阵子,五柱爹已有几多日子没得地瓜烧老酒入肚了,巴望着二十九号才开饷发工资。
五柱爹瞅着银柱在捡拾落地的书和笔,想着裁缝赵连景的那张白皮脸,火气涌上心头,破旧大头皮鞋一脚猛地朝那书那笔踏去。
五柱爹当时的确不曾想到,自己这一脚破旧大头皮鞋踏上,不仅使栓柱的那本狗啃猫嘶般的烂书变得粉碎不堪,而且使银柱的这只左手落下了终生残疾。
当时,五柱爹脚上穿的是早年捡来的一双破旧大头军皮鞋,足有三五斤重的大头军皮鞋盛载着上百斤的脚力狠狠地踏下,仅这一脚,便将银柱细小干瘦的两根手指骨踏成了粉碎。
银柱无疑是条汉子。银柱吊当着左手两根滴血的断指,大气憋回没吭一声,豆儿般大小的疼汗和眼中的泪水一齐滚下,摔在了书本上。银柱用那断指的左手,抹去书本上的疼汗和泪水,却在书本上留下了两道鲜红的血迹。
断了两根指头的银柱,两只小鼠眼喷着怒火一般死瞪着五柱爹。五柱爹一脸的凶神恶煞却佯装心安坦然,口里骂道:“怎么?小兔崽子,还敢打老子怎地!” 五柱爹真想抡起老茧巴掌狠狠地再搧银柱两个耳光。
银柱扬起滴血的手,狠狠地将指血甩在五柱爹的脸上。十四岁的银柱将满腔的怨恨射向了五柱爹:“你!你不是我亲爹!”银柱说完这话,五柱爹竟然奇异地一声没吭。
当时五柱妈没在家,五柱妈爱窜门子拉老婆舌家长里短说这儿道那儿的。那时,五柱妈肯定又是在裁缝赵悦景那儿缝制小布块儿,本来五柱妈也是可以带回家缝的,但五柱妈巴望着有时能够白吃人家一顿中午饭,也时常瞄准机会,拎件破烂衣裤叫赵悦景帮着改裁,大改小再穿,小接边还穿,五个柱子一茬茬地挨着轮着。
那天,五柱妈闻讯赶回,一进门,抱着银柱的残手大哭大叫,撕心裂肺地大骂着五柱爹:“你个老东西,你个狗东西,你不要二柱子的小命啦,二柱子不是你亲生的呀,你怎么就能下死手打他呀,你怎么就能废了二柱子的手指头呀,你个老东西狗东西,俺今天就跟你拼了这条命算啦,俺也不活啦,你把俺和二柱子一块儿打死吧……。”此时的银柱,头一次感觉到五柱妈为自己送来的一丝暖意,不由地心头大热,眼泪哗哗地滚落下来。
五柱妈从来没有这样撒野这般凶悍地对待过五柱爹,歇斯底里地直骂的五柱爹狗血喷头,又拎起拳头没命地朝五柱爹壮实的身上猛捶猛擂。五柱爹的麻脸木然着,站在那儿一丝不动地接受着五柱妈的处罚。
那夜,五柱爹叫花花下地跟金柱挤在灶坑前的烂棉絮里,由金柱搂着她睡,银柱躺卧在五柱妈怀里,五柱妈擎着这只残手为银柱解疼。
五柱妈当着五柱爹的面,像前几日给金柱冲白糖水那样,但这次是果断地从盛着小半罐白糖的罐子里舀出一大勺白糖,用暖瓶里的热水冲了,拿着小勺,一勺一勺地喂给银柱喝。
银柱手疼的怎么也不喝,五柱妈怕白糖水冷了,起身挪去炕梢儿,端着大半碗白糖水去喂了栓柱锁柱。那天夜里,栓柱锁柱双双害了感冒,两张小脸烧得一样地通红通红。
这一夜,五柱爹也没合眼,披着破皮袄坐在炕沿儿猛劲地抽着蛤蟆烟儿,满屋子叫五柱爹的蛤蟆烟儿鼓燃的烟雾弥漫乌烟瘴气。
银柱的断指疼得叫唤了一宿,叫唤的叫五柱爹抓心挠肝的心烦。五柱爹冷丁想起,那年为给五柱妈发奶哺乳金柱,用土枪打野鸡走了火,血淋淋一脸枪砂使自己变成了麻脸的大疼大痛,五柱爹宽容了银柱。从这以后,银柱的两根指头便落了残疾。
银柱断了两根指头很快就传遍了坝岗街,盈斋爷一大早就过来送给五柱爹十块钱,五柱爹推托着说:“盈斋爷,不要,哪能要……。”盈斋爷冲着五柱爹吼道:“我说他五柱爹呀,你是不是不要你那张老脸啦?这是给你打酒喝的还是买烟抽的?这不是叫你赶紧带着二柱子去医院用的嘛?看把你能耐的,瘦得猴儿似的娃子你也下得了这般重的手,二柱子不是你亲生亲养的呀,还是当爹的不是……。”五柱爹叫盈斋爷数落的一声不吭。
二顺爹歪在炕上,摔折了的左腿养伤也差不离了。二顺爹一听五柱爹竟然如此凶狠地对待自己的儿女,立马就要过去找五柱爹理论理论。二顺娘说:“你别过去了,虎毒还不食子呢,你咋就知道五柱爹那是有意的,人家八成也是伤着心呢,你再去数落人家,好吗?”二顺爹听了二顺娘的话,觉得蛮有道理,就说:“要不,你过去看看吧,跟桂月要一块钱,就说爹跟她借的,看看咱家还有没有鸡蛋票,给老五柱家二柱子买二斤鸡蛋送过去。”
自从二顺爹中秋节摔折了左腿卧炕养伤,一个人扑扑拉拉占了半边炕,家里睡不开,狗样就去盈斋爷那儿借宿了。二顺也要去,二顺娘不让,说是怕让这个刚刚被金叔金婶定为四类分子的给教唆了,狗样已经长大成人,是不怕教唆的。
二顺爹听二顺娘说了这话,立马对二顺娘说:“瞎说啥呢?咋能这么说话?盈斋爷何时抱咱家娃子落了苦井还是走了麦城?可不敢再说这话啦,人不能昧着良心,话不能望风扑影,听没?”又对二顺说:“你娘说的那些混账话你别听也别往外说,全都是混账话,二顺你记住,咱这条坝岗街上,盈斋爷要是坏人,怕是好人也就不多啦。”
其实,狗样在盈斋爷那里借宿,爷孙俩晚上没事儿唠闲嗑,盈斋爷传授的无非过去坝岗街理教公所的那些真言善语:迈左脚,进善门,进善门,一家人……。
狗样学识少,才念初中,脑子又愚,便对这真言善语顶礼膜拜,时时以真言善语为准,暗自数着自己的脚步,看从任何一个地方到旺叔家或秀女家,是左脚先入门还是右脚先入门。
每每,狗样进旺叔家都是左脚先入门,于是便觉得翠芝珠黑眼亮眉如新月腰肢曳曳神态楚楚而使狗样神魂颠倒;每每,狗样进秀女家也都是左脚先入门,于是便看着秀女唇似绽桃含情脉脉粉臂展展亭亭玉立而令狗样难以割爱。自然,翠芝的一草一木对于狗样这个青春勃发的半大汉子定是如铁遇磁;然而,秀女那初开情窦对于狗样这个新尝爱意的年轻后生又是爱恋不舍。
狗样糊涂了,好在没有谁发觉狗样的心里秘密。二顺爹和二顺娘仍然把他当作孩子一般,而旺叔也依然认定狗样就是他的合伙同盟。
旺叔嗜酒如命,一日两顿,一顿能喝半斤,酒足后叼上一支万里牌香烟,解放牌大汽车照样在大国道上飞奔,整夜开车也不瞌睡犯困。旺叔只要老酒入肚,气嗓门儿就变得老粗老大,喊着翠芝去干这儿的,吼着翠芝去干那儿的,翠芝丝毫不敢走样,她怕旺叔的拳头。
旺叔喝酒,他说自己从来就不知道酒醉是什么滋味儿。但是,那年的大年夜,旺叔确实醉了。
大年三十过晌,还没到吃年夜饭的时候,坝岗街的这帮二茬小子们都聚在旺叔家的炕上玩扑克牌赢小钱,一截两瞪眼的玩法,庄家摸出两张扑克牌,反扣,押家猜大猜小,一次押一分钱,输一赢二。
宝祥前前后后输了一毛二分钱,在那儿要哭鼻子,旺叔见了,气哼哼地吼道:“孬种!狗屁大点儿的小事就顶不住了,你旺叔这辈子的天都塌了,这日子不是照样还得过下去吗?”
狗样当时听了旺叔这话,有些不明白,只以为旺叔那是在臭埋宝祥顶不住事,才一毛二分钱呢。过后,狗样才从翠芝嘴里知道,旺叔那是自己在说自己的。
旺叔爹娘死的早自小在孤儿院长大,没人管教放任自流,十三四岁起就开始抽烟喝酒,过量的嗜酒吸烟造成举而不坚没能给金家传宗接代,不得不娶了已经怀上金叔种子的翠芝,生下凤儿掩人耳目。
大年夜,在旺叔心里,这一切都是该向列祖列宗交代的呀,因此,旺叔胸中满腔不悦心里痛苦不堪。
一夜连双岁,子时分两年。坝岗街西头四合院噼里啪啦鞭炮炸响,旺叔心头一震,知道年夜饭前为祖宗发纸祭奠的时辰到了。于是,着令玩扑克牌赢小钱的这帮二茬小子们各自回家,给祖宗磕头吃年夜饺子去。
旺叔没让狗样回家,叫狗样留下跟他一起喝酒吃饺子。
旺叔家供奉的祖宗跟金叔家供奉的祖宗当然是同一祖宗的,旺叔似有感慨万千的样子,在供奉祖宗牌位前双手虔诚地奉上三柱高香,然后“噗通”跪下,郑重地磕了三个头,口中似在念念有词,叨咕了些什么,狗样听不到。旺叔叨咕完,依然在那儿跪着,都老半天了,狗样哈腰朝旺叔看了看,见旺叔竟然泪流满面,狗样心里有些发慌,对旺叔说:“旺叔,供奉祖宗是个仪式,不需这般的呀。”说着,赶忙拽起旺叔。
起身的旺叔回过头对翠芝说:“今年你算是头一回在咱金家过年,也是头一回见祖宗,该给祖宗奉香磕头啦。”翠芝听了,缓缓地走过去,也像旺叔那样,在供奉祖宗牌位前双手奉上三柱高香,然后跪下,磕了三个头,翠芝没有对祖宗牌位说什么,做完了这些,只是站起身来,要去外间炒菜煮饺子。
旺叔问翠芝:“没对祖宗说点儿什么?”翠芝一愣,赶忙说:“俺说啦,说子孙辈的世旺媳妇念着祖宗,想着祖宗,求祖宗保佑着呢。”旺叔听了,没有言语。
翠芝炒好了菜,煮好了饺子,又一一端了上来。
旺叔给狗样倒了小半碗酒,自己倒了半大碗,旺叔将半大碗老酒一口喝的净光,吃了几个饺子,又倒了半大碗,还是一口把这半大碗老酒喝的净光。一旁的翠芝就劝旺叔少喝点儿,两个大半碗老酒下肚,旺叔便有了些语无伦次的状况了。
旺叔见狗样的小半碗酒还没动,自己就又倒了第三个半大碗,一手端着酒碗,一手拽着狗样要跟他碰碗。旺叔冲着狗样吼着:“喝!旺叔给倒的酒还不喝呀,咱今晚,人团圆,天圆地方过大年,喝他个一醉方休,喝他个万事皆无,喝,喝……。”说着,又瞅着炕沿儿坐着的翠芝说:“你叫,叫他喝,喝……。”翠芝朝狗样使了个眼色。
狗样学着旺叔的样子,端起酒碗仰脖吞了一口,辣得直吐舌头。旺叔见了,哈哈大笑,端起酒碗又是一饮而尽,然后夹起一方大肉,没头没脑地乱嚼一气。
旺叔大肉嚼过,喉头一动,冷丁冲着坐在炕沿儿吃年夜饺子的翠芝厉声吼道:“小荡妇!你,你说……,凤儿,是不是那人的种!是不是那人的种!是不是!是不是!……”
听了这话的翠芝,两眼直突突地发着颤,极度不安地瞅着旺叔,嘴里懦懦地:“狗样兄弟还在这儿,又是大过年的,咱不说这,好不?”
旺叔大吼:“什么?不说?不说,金家祖宗怎么会知道!不说,怎么知道我对你的恩典!要是都不说,四合院那人不是照样把老子当作乌龟王八吗!”旺叔这时激动得浑身颤栗不已,酒精的力量把他周身的血液烧得有些沸腾。
这时的旺叔真就有些歇斯底里了,扔下手里的筷子,“腾”地从炕上站起,一把揪住翠芝的头发,狠命一拽,将翠芝摔在地上,又怒吼道:“你说!那院子的鞭炮都炸响啦,你对着金家祖宗说,你玷污了我们金家!你对着金家祖宗说,你玷污了我们金家!刚才跪在祖宗面前你怎么不说,不说就不存在这事了吗……。”
这时的翠芝一声不吭,从地上爬起,依偎着门框,脸上显出木木的无奈。
旺叔还要再扑向翠芝,但下了肚的几大碗老酒在他胃里似在翻江倒海,猛地“咯嘎”一声,一腔酒食从他口中直喷大泄,旺叔就地蹲下哇哇地连吐,吐够了又在那儿嚎啕大哭,边哭边痛骂自己瞎了眼,边哭边痛骂自己有愧于祖宗。
翠芝看着一屋狼藉的呕吐臭物,赶忙过去,先将旺叔的一大摊呕吐臭物扫起扔出门外,又将炕桌上的杯盘碗筷一一拣下洗净。
狗样见旺叔还蹲在地上,赶忙扶起旺叔,弄到炕上躺着去了。
旺叔歪躺在了炕上,嘴里还在那梦呓般地叫骂,骂着骂着声音渐渐小了许多,而后就渐渐地变成了猪似的大鼾。
狗样担心大鼾后酒醒的旺叔再振作起来殴打翠芝,坐在炕沿儿就没走。旺叔猪似的大鼾越来越响,惊醒了凤儿要吃夜奶,翠芝赶忙洗净了手,侧身躺在炕梢儿将衣襟解开,风儿安静了,旺叔仍然大鼾不止。狗样在那儿琢磨着旺叔刚才的那些话。
狗样压根儿就不曾想到,这时的翠芝竟然放下奶着的凤儿,一把将他的头搂在怀间,一腔烫胸裹紧了他的脸,声音十分坚定地说:“狗样兄弟,你来吧,给我一回,当着你旺叔的面,这就是我的第二回啦……。”翠芝搂着狗样的脑袋,身子向后一仰,使狗样趁势俯在自己身上。
挨上翠芝身子的狗样,周身一阵燥热,慌忙地一高大跳蹦下了炕,两眼愣愣地瞅着翠芝,心慌的突突直跳。
也不去掩怀的翠芝盘腿坐在炕上,脸色煞白,两眼呆呆,没有丝毫的表情。
翠芝静静地对狗样说:“狗样兄弟,今天嫂子也不怕你笑话啦,凤儿是像你旺叔说的,是那人的种,嫂子是有了凤儿,那人也没了法子,才叫嫂子跟你旺叔拜堂成了亲,嫂子不撒谎,当时就对你旺叔说了凤儿的事,你旺叔是乐意的。嫂子哪里知道,跟你旺叔结了婚,嫂子的苦衷才刚刚开始,刚才嫂子要给你,也是真心实意的,嫂子这辈子到现在也就跟那人算是做了一回女人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别看你旺叔在,嫂子如同天天守空房,日日活寡妇一般呀,这都是你旺叔的无能。狗样兄弟,嫂子从没有得到过男人呀,你说嫂子有多苦,嫂子还年轻,这辈子该怎么过呀……。”翠芝说完,已是泪流满面了。
也就是在那时,狗样算是从翠芝嘴里真正知道了旺叔和翠芝结婚确实是金叔的主意,坝岗街人说凤儿好歹也算是金家的种儿,而没种到外人田里那话,在狗样这儿算是有了认证。
那时,翠芝好像还对狗样说着什么,冷丁旺叔就醒了,一咕噜从炕上爬了起来。
旺叔是让那几大碗老酒变成了一泡尿水给憋醒的,毛毛愣愣地起身便趔趔趄趄往外走,刚踏出门坎的旺叔“扑腾”摔了一个大跟头,狗样和翠芝急忙出屋,见旺叔脸朝地背朝天地摔了个实实惠惠,四脚八叉的旺叔身底下卧着个长拖拖的大黑物。
翠芝狗样都慌了,狗样拽拽旺叔,人是醒着的。旺叔冲着狗样,指着身底下说:“这,这,什么东西绊了我一大跟头啊。”狗样朝旺叔身下定睛一看,惊叫道:“妈呀!”竟然是一条大狗长拖拖地睡在那儿,挺肥挺肥的,憨憨地卧在旺叔身下死死地睡着。狗样赶紧扶起旺叔,那大狗仍卧地不动睡得安详。
翠芝猫腰细一瞅,突地叫道:“我的妈呀,这大狗怕是吞食了你旺叔呕吐污物也醉在那儿啦!”这一嗓子使旺叔猛地清醒过来,大叫道:“什么?狗也醉啦?狗也醉啦?哈哈……。”
大笑中的旺叔突然止住,小声地有些神秘地说:“狗样!合该老天照应咱,把它弄……,弄回屋去,宰了它个狗东西!”
旺叔什么也顾不得了,朝墙根儿哧净了这泡尿水,回身进屋从水缸里舀了半瓢冷水咕嘟咕嘟灌下肚,瓢一扔,吼道:“拿斧子来!剁了它个狗它娘的,过个好年!送上门的香肉……。”
旺叔找了根绳子叫狗样帮着把醉狗捆了个结实,狗头按在地上,举起斧头,“噗呲!噗呲!”三两斧子剁下了狗头,那醉狗连叫也没叫,登时淌了一地血就没了气。
旺叔叫狗样烧了锅开水,旺叔动手,不大功夫,狗毛褪净,扔进炉火里烧了,一只白条条的狗肉摆在那儿啦。
翠芝瞅着那死狗,对狗样说:“这,这,不会有事吧……。”旺叔听见了,吼着翠芝:“臭嘴,大过年的再说不吉利的,把你也剁了去。”翠芝瞅着狗样,眼泪哗哗地掉了下来。
旺叔硬是只留下一条狗腿连着的半条狗脊梁,剩下的都叫狗样拿回家去,旺叔说:“过年了,二顺家人多,少了不够吃。”
狗样拎着大半条白白净净的狗肉回到家里,二顺爹看了,惊讶的眼睛瞪得老大,二顺娘急急地问狗样:“那儿弄来的?”狗样说:“一条醉狗昏睡在坝岗街上了,就跟旺叔俩给收拾了。”二顺娘说:“还有这好事?”三顺四顺跳着叫着要吃狗肉喝狗汤,桂月说:“娘,俺咋不敢看呢,白条条的还缺了一小半。”狗样说:“姐,旺叔就留下那么一点儿,剩下的都在这儿呢。”
狗样拿刀肢解了白条狗,攥着一条狗腿悄悄地跟二顺娘商量要送秀女家去,二顺娘点了点头,笑着说:“还有两条狗腿,想着叫你给老五柱家也送去一条咧。”
狗样两手提着两条狗腿出了门,二顺爹笑着对二顺娘说:“哟哟,瞧瞧你儿子,几时也晓得些礼数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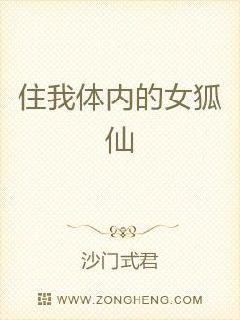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