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来的食》最新免费章节第五章王宝钏与薛平山
第五章 王宝钏与薛平山
“出村男儿莫回乡,乡土地薄养人愁。几亩庄稼赚个啥呦!炕头凉,一穷窝,婆娘谁稀罕瓦窑洞!”
开往沪市的火车,需要先坐县里的大巴到城里候车。一趟一人一共一张红票子,够抵得上李家村一户人半个月的收入,那票攥在乡下娃子手上,心疼得能让肝胃直哆嗦,甚至腿不听使唤地想往退票口走。
但李土根画的饼很香,使他们像闻到肉味的山狗使劲往大巴里钻。等大巴车一开动,再想后悔却是人已经跟着车一块颠簸晃悠。上完坑坑洼洼的山路,直上高速公路,按路程算,司机说起码开上三天两夜。
27座的大巴车里弥漫着一股刺鼻呛人的烟味,坐在大巴车里的27人就两个人在抽烟。一个司机,一个带了6个同村的李土根。李土根抽的是十几块的玉溪烟,但他就上车给司机递了一根,自己抽了一根。此后,在车上,抽的全是同村人递的陕西烟,比如猴王。
一根接上一根,不嫌多不嫌少,一唠嗑接一唠嗑,什么初中辍学、外出打工、混迹沪市、小小工头等等标签,李土根自话自说地给自己贴着。据他侃,他这次回村,是代他的包工头招工;据他吹,他这次回去,起码被包工头升工头,管这片子同村人。
因此,他不喜欢同村的人唤他小名“土子”,也不喜欢人叫他的名字。为此,他费了大概三十分钟的唾沫纠正同村人的称呼问题,统一改叫他新的名字——李图昆。显然,在大城市呆久了,跟“土”沾边的名字,老遭人嫌弃,叫不出口。
一路上,车在沥青路上开着,太阳从那头移到这头,靠窗的沈清曼至今没跟离三说过一句话,面若冷霜,一味地吃着他递过来的干枣、烙饼。
李土根眼角余光瞅到离三,努努嘴示意围在他四周的同村人朝离三那边看去,大声向他调笑道:“瓜皮,是不是秦川人的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专疼媳妇的沪市小女婿呢!”
同村的人却不敢笑话离三,一个个噤声,倒让李土根的癫狂嬉笑更加衬托四周诡异的沉默。李土根发觉到不对劲,慢慢由跪贴在椅背改坐在座位上,左右四顾,对众人的不理睬不满而又好奇地问:“你们咋不笑,难道额几年没回来,李家村带把的都惧内了?”
“土,不对,图昆,他是李三啊,你不认识他勒?。”有人见李土根忘记离三是谁,好心提醒。
李土根听到“离三”二字,一愣神,在同村人围观了几秒以后,指尖夹的香烟被他一哆嗦弄掉在地上。李土根立刻把烟踩灭,手扶住椅背,朝离三方向连连哈腰点头,道歉说:“原来是离三兄弟,你看老哥这记性,竟然忘了把你也招来了。嘿嘿,你抽烟吗?”
李土根忙从t恤衫的口袋里把那盒玉溪烟掏出来,刚想叫人传一支,又觉得不妥,咬咬牙打算把整盒进献给离三。
沈清曼一言不发,她心里清楚同村人之所以怕离三,是因为流传着一段关于他的传闻——村里从前有一个二流子,看离三面上老实巴交,想拿他立威摇旗,混个名声。所以,有段时间里,他动不动辱骂离三,一逮到他就使劲地捶着欺负,不过离三呢,依旧憨笑容忍,直到他一次话里头连带着连累李婶、爷爷一块受骂。
自打那一次以后,二流子就突然不见踪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村里再也听不到他的骂声,当地公安立案花了两年也没能找到这个尚未注销的失踪人口。
但这并非最为这些晃悠流荡在县里高中的地皮流氓忌惮的,他们更顾忌的是,是从李家村出来的传言——
据白天到山上砍柴的李铁柱说,他曾经在山上赤手空拳,遭遇过一头重达190公斤的发情母野猪的袭击,李铁柱当即吓得拔腿就跑,一溜烟工夫他蓦然回首,就见离三非但没跑,反而迎上去,像武松打虎般,抄着家伙在一个劲儿狠揍粗皮厚肉的野猪,打得野猪竟满地乱窜,窝囊地往深山里跑。
之后,目瞪口呆的李铁柱眼睁睁瞧着离三追进了深山老林。再见着离三,是傍晚黄昏他下山的时候,那时,村里人和他李铁柱一样,目睹他扛着口吐白沫的野猪到村口,接着在那一天晚上,村里的家家户户热闹非凡,磨刀霍霍,烟囱冒烟,都烧着火变着法吃野猪肉。
再然后,满嘴油腥的悠悠之口把离三斗野猪,越描越神,天花乱坠,乃至夸张得快成神话,也因此听过的但没见过的,将信将疑,只当是一个传言。只是,李土根嘴里貌似还记着那野猪肉的味道。
“我不会抽烟,烟就算了。”离三斜视旁边的沈清曼,留意到她掩住口鼻,流露出一副对车里烟味厌恶的神情,他朝李土根说:“土子,你也少抽点。”
“好的,好的。”
李土根坐回位子,赶紧把耳朵边的烟取下来,放进烟盒里,然后整包塞回口袋里,不打算再碰。接着回头瞄了眼闭眼小憩的离三,他轻呼一口气,跟其他李家村的人又聊起了其它的话题,似乎刚才的一幕没有发生过一样。
……
大巴车从早上9点出发,司机到12点歇了一班,再到夜间8:00,彻底停靠在一家与他们公司有合作的旅店。
旅店有30间单人房,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况下,哪怕司机是不是有意无意地开到这里,哪怕旅店是不是一家宰人的黑店,除了极少数拖家带口实在没办法睡车里的,大部分包括李家村的人在内,都横不下心花这“冤枉钱”,一个个宁愿整宿躺车里,也不嫌闷臭。
老板在招待台的玻璃窗后面,在他身后的墙壁上挂着尚未租出的房间牌号,他们夫妻俩一位一位地收钱登记。忙着反复清点钱款的老板很少抬头,操着一口带湖南夹杂赣江的口音反复那几句说:“一间房80,住到明天9点。住几间房?”
离三手里提着两口装书装衣服的箱子,肩上背有沈清曼放里头的衣服、棉被、枕头等等的行李袋。他前面的人刚刚领了一把钥匙走。轮到他时,老板忽有一种黑云压城的感觉,惊得猛抬起头,见是一对男女,握着笔的右手指了指右窗口,说:“80,去那头领钥匙。”
“老板,要两间房。”离三忙握住去接钥匙的沈清曼的手腕,从兜里掏出两张大红拍在台前。
“确定两间房?领了钥匙,可概不退款。”老板瞄了眼离三,瞅了眼沈清曼,觉得古怪,但没多问,再次提醒离三。而当墙上的挂表走了几秒,老板见离三没抽回钱,嘴角一扬,拿笔“唰唰”在簿上滑了几笔,另一只手伸过去拿钱。
“一间房。”沈清曼出现在老板面前,在他发呆于自己清冷秀逸的姿容之时,她从窗口里抽回一张大红,今天头一回跟离三搭话,说话清冽。“别白浪费钱。”
老板虽然纠结于少赚了一百,但更好奇于离三的犹豫,暗想这小子生在福中不知福,要搁自己有这样俊俏媳妇儿,那恨不得天天压在她身上耕田耕到老牛死都甘心。他边意、淫,边斜眼瞥了眼不远处的自家丑媳妇,顿生嫉妒,不满地催促说:“你们到底要一间还是两间,后头还有人等着呢!”
沈清曼将钱塞入自己的兜里,瞪视准备再次掏钱的离三,捏住他的袖子拉到拿钥匙的窗口,用毫无商量余地的口吻命令他去取钥匙,接着转向看他入迷的老板,清冷地说“找20。”
房间在二楼,二人走过挂在墙上告知旅客的注意事项和水电安排,沿着弥散尿骚臭味的走廊找到209号。
“咔”,“啪”,门开灯亮,整个房间的布置站在门口便能看完。20左右平方,一张铺着绣有花的粉色床被,右边是床头柜,上面正对空调,门对面则是四扇窗户,窗帘则用流苏裹住拉到两侧。
“进去啊,堵在门口干嘛。”沈清曼推了一把离三的肩,离三“哦”的一声,提着箱子扛行李进屋。
“砰!”一听到关门声,离三有些胆怯地回望在打量房间的沈清曼。
沈清曼穿过离三身边,径直把窗门打开通通风,回过头却见离三傻站在原地,似乎正盯着她的背影。她心里一突,所幸没表现出来一丝慌神,故作淡定地捋了捋散乱在鬓角的几缕青丝,双手紧握于胸前,嗔怪道:“还傻站在那干嘛,还不把行李放好。”
白炽灯照射下的玻璃里映有沈清曼娇美的容颜,也映有正在摆放行李的离三的侧影。望着玻璃上的他,沈清曼眼波潋滟,目光复杂。一路上,正如离三所说的,随着离沪市越近,她的心态跟着不断变化,昨夜对离三那种近乎炽热的爱,现在也冷淡了许多,她开始更加冷静理智地审视理清二人之间的关系。
他于她,到底是日久生情的情人,还是再造之恩的恩人,没准兴许只是相敬如宾的“姐弟”,不管怎么样,中间总始终树着一个沈家。沈清曼思绪良久,想得迷离,想得愁怨,丝毫没有察觉到已经来回公厕一趟取水的离三。
“姐,洗脚吧。”
离三提着一红桶的水,热气腾腾,桶的边缘各摆有一条自家里带来的洗脚布。沈清曼轻应了一声“嗯”,像青梅竹马,或者亲如姐弟般,任由自己的脚底贴在离三的脚面,脚拇指对脚拇指地触碰着。可每触碰一下,再想起昨夜的爱恨纠缠,两人都莫名感觉心头有一条丝线牵扯彼此,共尝悲喜甘苦。
“倒了吧。”已经满脸红晕的沈清曼努力寒着脸,拿洗脚布轻轻擦拭自己的脚以掩饰内心的害羞与紧绷,细声呢喃。
离三哒哒地踩着旅馆提供的凉拖往外走。
等再回到房间时,发现窗户关得只剩下条细缝,靠墙的一侧床上有个鼓囊囊的把床被支起。离三尽量压低声音,锁上门关上灯,杵在门口迟疑了片刻,才扭扭捏捏地缩进床头的另一侧,与沈清曼共用一个枕头。
鼻嗅伊人的兰香,背靠伊人的软背,感触伊人的颤动,离三难以入眠,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又过了一段时间,走廊里传来老板娘的声音,她正挨门挨户地敲门提醒关灯时间到,敲门声不大,估计吵不醒熟睡的房客,倒使得久难入睡的离三愈发精神。
他深吸一口气,沉入丹田,与腹中的那团火热负隅顽抗,同时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觉,却不曾想脑海里竟全是与沈清曼朝夕相处的生活片段,它彷如影片般在放映机的播映下,一个镜头接一个镜头的变换衔接。
沈清曼也不怎么好受,由于蒙在被窝里许久,里面的沉闷她再也忍受不住,慢慢露出头喘息着气,既想又不敢翻山辗转,和离三只好在1.5米的硬板床上背对背亲密地贴着。
“姐,你睡了吗?”
离三还是睡不着,既怕耽误沈清曼休息还怕她误会,因此说的声音很小。而这,还是令沈清曼神经一紧,心跳加速,全身僵硬,双腿绷直,浑然没有察觉到与离三贴得愈加紧。
离三故意抬高些声调又试了沈清曼几次,感觉背对的她没有动静,以为已经睡着,顿感心安,不由敞开心扉,喃喃自语:“姐,你一路上不跟我说话,也不再开口唤我‘三儿’,是不是为昨天晚上的事儿?”
沈清曼唇齿微动,连自己也听不到自己张嘴说出了个“是”,因为太心虚。此前情意的倾诉未能圆满因果,两人之间的关系已是极其的尴尬,要说他们俩是既做不成清白干净的姐妹,又做不成柔情蜜意的情侣。彼此的隔阂,早伴随距沪市的路程越来越短,不单显得越发难以消除,更是渐渐地演变成鸿沟深渊。
“其实姐,昨天听着你给三儿说的话,三儿是真想一冲动,把你一直留在我身边,哪怕洪水滔天我也不管,更想像你说的那样,生米煮成熟饭,按戏文里的,让我这个张君瑞作你崔莺莺的夫君。可是,我还是那句话,我想,可我不能。这里面虽然是有沈家的关系,但我发誓我不孬不怂,因为这儿就畏畏缩缩。我只是出于对姐的尊重和怜爱,不想姐一直没名没分地跟着我过日子,有娘家却不能回。”
离三说得愈发动情,沈清曼听得愈发揪心。胡思乱想、心有郁结的她听着离三的自白,床单被她紧紧地抓住又轻轻地松开。她改了姿势,蜷缩在一小块地,膝盖抵在下颌,长长的睫毛随眨动的眼睛微动着,眼眶里流转着一泓泪泉。
离三能听到被子微微翻动而发出的窸窣声,在黑灯瞎火中,他扭头瞄枕边人一眼,发觉她很快没了动静,以为只是改变睡姿。
“姐,我不知道你和他们嘴里所谓的沈家,究竟是什么情况。但至少,三儿知道,你从不是一个普通的南方女人,你总是能随意地说出几个我从未在县城里见过的东西。蓝山咖啡、宝格丽、路易威登、范思哲……”
回想起与沈清曼的朝朝暮暮,离三觉得沈清曼酷似一只风筝,一只被他用线头牵着,飞得日益高的风筝。起初他还在兴头上,没在意狂风呼啸,可等到线头拉得越长,已经长到自己收不回来时,才明白它原来可以离自己这么远,可以离天这么近。它一直就这么挂在天上俯视自己,让离三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想吃天鹅肉的蛤蟆,而且即便成精可不会腾云驾雾的话,是永远拿不回她。
“我们的差距就像地主老财家的黄花闺女和贫下中农家的贫贱小子这么大,”离三说的时候不卑不亢,跟他的腰板一样直。“要能娶到这样的媳妇,搁谁谁不想呀。可要想真娶到你,地主老财哪舍得。姐,说实话,我想过好几种法子,最直接的就是想当土匪,把你掳走霸占了作压寨夫人……”
躲在被窝里暗自饮泣的沈清曼,在离三一波又一波的真意情话下,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发出一阵又一阵沉重又愈发响亮的抽泣声。终于被离三留意到,他一脸难堪,支支吾吾、吞吞吐吐地问:“姐,原来你没睡着啊?”
突然,离三感觉到脊背袭上一股滚烫的热气,那东西尖尖又软软的,柔柔的又暖暖的,它像是鼻子,像是嘴唇,像是额头,他知道沈清曼正将整张脸贴在他的后背摩擦。此刻的离三,底气不足地轻问了声:“姐?”
“三儿,说下去,说下去。”沈清曼蜷缩着,单手搭在离三的肩上,两只玉足则在离三的小腿内侧附近亲昵地游走,似是奖励。
“但我不想做匪,匪就是匪,不造反、不招安的匪永远上不了台面。况且,我不想让姐过舔血又吊胆的日子。”离三顺应心境,深情款款地说。“说实话,上门女婿、王侯将相种种,我也想过……”
“三儿怎么会作上门女婿呢!你从来不是吃软饭的料,你能翻江倒海,自立门户,你会光耀门楣,蒙荫后代,所以千万不要再说这些话。”沈清曼将离三搂得更紧,缠得更深,温柔细语,“三儿,还记得老村长唱的《五典坡》吗?”
沈清曼死死地扯着离三的衣角示意他翻身,而离三早就按耐不住心中的火热,在被子微微的窸窣声下,两个人相拥在一起,你吸着他吐出的热气,他受着你传来的情意。
沈清曼靠在离三坚实的胸膛里,轻哼唱词:“姑娘哪晓得来路情,贫生把话说分明。我家住陕西长安城,父母双亡身伶仃。若问贫生名和姓,薛平贵本是我的名。”
离三对薛平山与王宝钏的故事可谓耳熟能详,稍微明白沈清曼蕴含深意的心思,配合地扮演起“王宝钏”一角。“听罢言来心自忖,观相貌总非贫穷人。”
沈清曼思维跳脱,在离三的耳畔边借台本中的唱词明志:“……是儿对天有愿,打中富贵人,作为富贵妻,打中贫穷汉,哪怕去行乞。打中胡儿去投番,要学个昭君娘娘怀抱琵琶去出雁门关。今乃打中乞儿手内,也是你儿命该如此。”
“姐,我懂你的心意。可我不想让你像王宝钏那样,在洞里苦等十八年,委屈你受苦。我想你在那座宰相府,那座目前对我而言是高不可攀的宰相府等我,等我骑白马,抬八抬大轿把你风风光光地迎走。”离三紧紧握住沈清曼的手以使她体会他的坚定与自信。
沈清曼又喜又恨情郎的固执和倔强,赌气地咬住离三的脖子,给他留下一排浅浅的齿痕,鼓着红腮嘟囔:“三儿,你个憨蛋,不管吃素还是吃土,姐说了,什么都愿意。”
“彩楼上绣球打中你,这姻缘算是天造的……”
沈清曼捂住离三的嘴,眼里氤氲一层薄薄的湿雾,借唱词表明自己的情意,也借唱词试图说服自己。喃喃又唱了一段,突然她心有定计,一反常态,颤声说:“三儿,那姐给你留着。”
离三感受她话语里暗藏的拳拳爱意,笃定地说道:“姐,我不知道我将来会怎样,但姐你放心。哪怕将来一无所成,真落草为寇,我也要拼命抢大户的红轿、夺土豪的家当,把你娶回山窝。但我保证万不得已,不会有这一出。
我誓要为你披星摘月,去争波澜壮阔,凑得照耀余生的星光灿烂;为你夙兴夜寐,去争千秋万岁,赢得陪伴残生的天长地久。姐,我一定要把你明媒正娶迎回我家。”
“三儿,那你要记得怎么去宰相府,别走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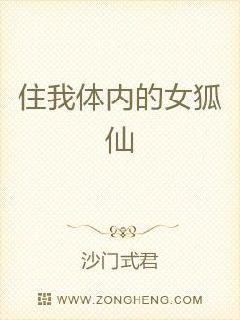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