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喊》最新免费章节第二章昔年记忆
第二章 昔年记忆
腊月二十过后,很多私营企业便开始张贴放假通知。细心的人会发现,这几天大家用的都是阴历纪年。
腊月二十三的晚上,我在玩《丝路英雄》,小逆在QQ问我:“听说你媳妇在广州,我们单位的年会在天河区举办,离她远不?”
“远倒是不远,就看你们开年会是几时,合适的话你过去了好请你吃河粉。”
“腊月二十六下午三点开始,到晚上十点。”
“那不成了,我从西安到桂林,她从广州到桂林,她腊月二十六上午出发。”
“哦,我明天十点的机票,要不你帮我提下行李吧,我爸开车送。”
“妹子早说嘛,早说哥跟行李一起走。”
第二天送完小逆,莫叔拉着我去边家村的工行取了车票,到铁志明买了五斤牛肉,在赵记买了五斤绿豆糕,两个人在大车家巷美美地咥了一顿东北小二丸子汤。
一路上看南来北往行色匆匆的人,他们的脸上挂满了年前的笑容。
湖南的冬天,湿润而阴冷,尤其到了夜间,浸入骨髓的寒冷似乎要把人体那点仅存的温暖带走,只留下一具勉强呼吸的躯干在漫长的夜里瑟瑟发抖。在这样的冬天里,人的思维仿佛成冰,什么情感,浪漫在刹那间都被抛之九霄云外。
对于牛婆岭的农家来说,最欢乐的时候,要算是年三十了。郭大圆在这一天穿了漂亮的鞋子和崭新的衣服,跟很多农家人一样高兴的合不拢嘴。
往常一到晚上十点钟,除了火车疾驰而过的声音,整个村子就都安静了。但是在除夕的夜晚,似乎连鱼塘的鱼儿整夜都在沸腾之中。
在春节晚会的精彩节目中,妈妈端了半箩筐的花生坐在餐桌前,用双手捧着分成四堆,爸爸、妈妈、郭大圆、弟弟各一堆。妈妈觉得很不均匀,便把自己的那份添给两个孩子,爸爸添给她们之后,就剩几十枚了。
“这是咱们四个人的花生,谁先吃完就没有了。”妈妈说。
“喔,不能偷吃我的花生。”郭大圆对弟弟一边说一边将花生装到自己的糖果袋里。
“每次都是你吃我的,还说我。”弟弟无辜的申辩着。
弟弟的手小袋子小,装不下的时候,就很不情愿的将剩下的花生推给郭大圆,“喔,给你,算是你帮我放牛的奖励,再多就没有了。”
郭大圆赶紧抓过来一边装一边剥开了吃“真好吃啊!”。
“喔,妈妈,这是给你的。”弟弟极不情愿的分出几枚花生给妈妈。
妈妈看着她们的样子,慈爱的笑了起来。
“爸爸,新年好,身体健康哦!”
“妈妈,新年好,身体健康哦!”
“新年好!”
“喔,新年好!”
新年过后,上学,放学,做饭,洗衣服,放牛,割草,喂猪,玩耍,写作业……
很快地,又到了年底,又是在春节晚会中过着欢乐的除夕。
妈妈照例端出半箩筐的花生分作四堆,弟弟看着郭大圆的那堆花生,不情愿的又多给了几枚:“每年都是你分得最多,吃的最快,今年给你多给些,不能再吃我的了。”
郭大圆笑嘻嘻的装起来,“真好吃啊。”“放心吧,绝对不会了。”
“爸爸,新年好,身体健康哦!”
“妈妈,新年好,身体健康哦!”
“新年好!”
“喔,新年好!”
在这样的祝福声中,一个个家庭又送走了除夕。
新年过后,上学,放学,做饭,洗衣服,放牛,割草,喂猪,玩耍,写作业……
除夕,春节晚会,爸爸,妈妈,郭大圆,弟弟,箩筐,花生,新衣服。
几年过去了……
妈妈已经不再在除夕的时候分开花生,而是念叨。
郭大圆给爸爸、妈妈送完祝福之后,跟弟弟说“今年有没有再给我留花生啊,哈哈,我吃不到你吃不完的花生哦。”
“留了,我去年留给你的花生都发霉了,只好扔掉了。”
时光匆匆,一年又一年,年三十又来了。
蔚蓝色的天空飘过几朵白云,舜皇山青葱浓郁,紫水河叮咚作响,清澈见底,绿树下的池塘里,鸡鸣鸭叫。穿过铁路,顺着溪流下行,大片大片的蔬菜香。
这时的牛婆岭,自神仙桥到鸡公堂,都是二层三层的房子,以前有天井的院子成了成年旧事。郭大圆结束了一天的拜谢,和妈妈在厨房里乒乒乓乓的做着年夜饭。
“郭大圆,你们快躲开,我要放烟花了。”我喊道。
烟花过后,弟弟在休息时间打来电话,电话中给爸爸妈妈送完祝福,郭大圆说道:“今年家里好多花生,你们又不回来,又吃不到了。”
“那就送给你,这些年留给你的,你吃不到,今年全送你。”
“嗯,真好吃!”
“喔,以前一到过年就嚷着给姐姐留花生,还说姐姐过年不在没意思,花生坏了还舍不得扔。”母亲在一旁插嘴道。
“……”
郭大圆一边剥花生,一边笑着掉眼泪。
门外,跳跃的爆竹拥抱了对新年的期许,在震耳的响声中祝福欢腾的来年。两个红色的灯笼高挂,灯光映照下的“福”字,在除夕的微风中,轻轻地摆动着,照向远方……
大年初三,郭大圆去吃喜酒,我在家看《小李飞刀》。小逆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聊天,她说外公家的小狗死了,我变得惆怅起来。
听说又下雪了。
北方的冬天,寒冷而又干燥。
哥哥从小姑家抱回一条黑色的小狗,很讨人喜欢。它很淘气,白天总是竖起短小的尾巴,亮一对大眼睛,跟着大狗,在庄基的周边巡逻。
大狗越来越老,已经吃不动食物了。除夕前,大雪纷飞的天气,村里的几个小孩玩爆竹,炸伤了它。萎靡的呆在茅舍,呆呆的望着飞舞的雪花。热闹的大年夜,小狗偷偷地叼了骨头溜出去,一定是给大狗了,它经常这样干。深夜的热闹中按照风俗迎接了喜神,在“瑞雪兆丰年”的年夜里疲倦的睡去,隐隐听到小狗在呜咽声。这时候,谁还管那么多呢?
大年初一,母亲隔着窗户喊我们几个壮丁起来清扫积雪。迷迷糊糊中极不情愿地套上冰冷的棉袄,其时妹妹在门外大叫起来:“妈,白狗死了”。大狗在大雪中静静的离去,盆里有几块未吃完的肉片,嘴角边散落着几块咬不动的骨头,小狗傻乎乎地蹲在大狗的尾巴后面,冲着我们叫,头顶粘结着未融化的雪块。难怪昨晚没有在卧室看到小狗,原来它陪伴大狗度过了在它自己极为悲伤的除夕。
读高中时,带一些食堂的剩馒头给小狗。小狗跳了起来,手舞足蹈地跟我亲热。空闲的傍晚,我便带了它,沿着山路,追逐着,打闹着,嗔怒着,奔跑着。小狗承继了大狗的事业,渐渐长大了。
有一年,为了防治狗贼,父亲制作了一副足够牢固的铁链,将小狗固定在它的茅舍。失去自由的小狗,不时在深夜里望月哀号,有什么办法呢?对一条狗来说,还有什么比生命更加宝贵呢?
大学后,便少了许多与它热闹的时间。偶尔在冬天,与几个擅长打猎的伙伴,背着自制的猎枪,解开它的锁链,在冰天雪地里包围山獾,网罗飞鸽,追猎雉鸡。当我们瞄准目标的时候,它胆怯的远远躲开,趴在雪地上,生怕自己被击中,一副胆小狗的样子。当它看到惊吓或者受伤的山獾在雪地里艰难的逃跑时,便一跃而起,飞快的追上去擒拿山獾,一副真勇士的样子。
一个夏天,我在边吃李子边打松鼠。母亲喊道:“凌碌,狗不见了,你快去找。”我在搜寻中,隐隐听到山坳里传来汪汪声,找过去时,它被铁链缠绕在一棵小数下,翘起尾巴,仰起脑袋冲着小树上的黑猫大叫。一定是这只黑猫又来偷吃,被它驱逐出境时激动地自己都没法解脱。解开铁链,它痛苦地嚎叫着,是一枚铁钉洞穿了它的前掌,痛哭流泪。我摸摸它的脑袋,看它温顺将铁钉拔了出来,小狗泪眼中伸出火热的长舌,趁我不注意吻到我的脸,热乎乎地,十分可爱。我摘掉铁链,鼓励它跛着脚回家,阳光照耀了移动中两个不同形象的影子:它越来越像个“男人”了。
毕业前,决定南下广州,我回家向家人辞行。低落忧伤的心情充斥心头,在干燥的黄土地上,带着没有铁链的小狗,在黄昏进行一次调节情绪的出行。也许只是静静的走了一段山路,在儿时经常玩闹的地方捏几撮黄土;也许是在劳动过的麦田里,嗅几下蔫巴的麦苗;淡忘的细节,无法忘记的场面。因为,在于我,心里无比清楚,它的寿命实在有限,轮回是迟早的事。事实上,那是小狗最后一次伴着我一起出行。
第二日,和父亲搭乘邻居的三轮车去镇上乘车,母亲偷偷的背过身子,在田地里使劲的揽起衣襟,小狗焦急的抖动铁链不停的吠叫。母亲的身影,在视线中模糊了,小狗的吠叫,在耳畔里隐约了……
在广州,常常向母亲问起家乡,不时问起小狗。到后来,母亲说小狗已经很老,吃不动食物了。我在想,小狗老去的样子是不是和年轻的时候一样:雄壮而又帅气。有一次,母亲说小狗又聋又老,不想看到小狗慢慢的老去,打算将小狗托给邻居处理。狗年出生的郭大圆疾呼劝止,那是母亲随口而说。无论如何,它的境况越发艰难起来,或许等不到我们回家了。
西北的冬天,如今已经不再是冰天雪地的情景,而是黄沙飞舞、北风怒号的景况。小狗或许是已经很难撑到我们回去,或许已经认为我离弃了它,在一个寒冷的黑夜选择了我以前带它捕捉雉鸡的山崖,跳了下去。父亲找到小狗时,它已经气息奄奄。父亲想办法下到洞穴想要带它回家时,它已经僵硬了曾经健壮的躯体,泪冰垂到地面,永远的闭上眼睛。伤感的父亲和热泪的母亲,一起动手掩埋了小狗,无限的失落。
2007年春节,我们回家,想起曾经雄壮的它,十分怀念。母亲给我指了它的所在,我一直没去,希望那种怀念那种遗憾,静静的藏在内心深处。
生命终究有个终点,小狗的离去是自己生命的终点。对于小狗而言,这是最后生命里最好的解脱。希望它在另一个世界里,能够想起我和它在一起的热闹日子,能够想起我和它在一起时快乐的时光,能够感觉到我在怀念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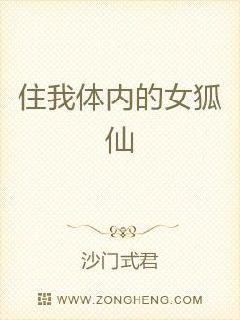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