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先生少年行》最新免费章节25.洪荒
25.洪荒
“你还记得橡皮的味道么?那种让人想咬一口的清香。”
——梁续(2020)
梁续带他们过夜的地方,叫爱马社。
听起来挺大气的,但跟奢侈品爱马仕一分钱关系也没有。
在天通苑的最北边儿,如果你把地图拉到最大,会看见有几条头发丝一样的路,却没有任何文字的标识。这里本就没有名字,唯一的地标是一家叫□□马社的汽修中心。
里面住的人却不少,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半截塔,再到霍营东边,是五环外出了名的城中村。
最早是几家工厂的集中宿舍,后来工厂搬走了,便被几个小老板盘了下来,搞出租房。生意不错,几家小老板都赚到了钱,于是越盖越多,合成了一大片。
每个院里的矮楼都刷成不同的颜色,用来昭示他们所属的不同老板。房间面积平均在20-40,挤挤能住不少人。租金就便宜了,即便在前两年这么高峰的时段,也能保持在一千八到两千多之间。
这个价位自然没什么服务可言,暖气自己烧,水管儿自己装,要是把走廊的地砖踩坏了,还要多掏些钱补偿。
梁续考研那两年,家里拖了北京的关系,以十几万的价格直接将其中一间买断,供他自己一个人复习用。
他习惯穿着一身绿色的珊瑚绒睡衣在小巷中溜达,他说这里有独特的“后现代乡村风情”:晚饭的时间可以在周围的夜市买到有鸡汤豆腐串和炸臭豆腐,炒饭炒面也不少。还有楼下的牛肉板面,每次都是现压的,配两个店里自己卤制的鸭头,一顿饭也能吃的热汗淋漓。
剩下多数的时间,他就坐在那块被桌布挡着的窗户前下面,听听评书喝喝茶,画画图,背背英语,倒烟灰的时候顺带想想未来。
结婚之后,他便和媳妇一起住进了大房子里,转手将这里租了出去。这看楼的大爷问别家都是收房租,只有给他是交房租,一个月两千,梁续还挺开心。
不过好景不长,两个月前,大爷来信息说昌平大拆迁,租户们都快走光了。梁续叹了口气,倒也没往心里去。
没想到,这时派上了用场。
三人将车开进巷子,幽暗中,是灰蒙蒙的一片,没有路灯,只有满墙的封条和告示发出的暗白。即便几个院儿的门岗里还有些光亮,除了远远的狗叫声外,这里的寂静更像是与这座城市绝了缘。
“梁老师,你这个地方安排的——”吴越咬紧了牙,本以为能发掘出梁续在北京的“温柔乡”,不想却是这么个地方。
“——挺特别啊。”
Sunny倒不做声,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满。
旧地重游,梁续痴痴望着那一片狼藉,竟有几分不舍。
那些阳台下,院中溜孩子的南方人,晾晒着白大褂的护校学生,新搬来的大学情侣,似乎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般。
他本还想着将来带孩子来个“忆苦思甜”,现在看,要不了几个月就会是一片平地了。
梁续看了下水电,尚还有供应,两张床板也还在。
吴越在客厅的椅子上坐了两坐,还是没忍心坐下去,推着梁续的胳膊肘把他带到了角落。
“这叫你他妈安排的地方?这他妈的能住人?”
“唉呀——”梁续也一脸的难堪,“我这不是没办法了么,你坚持一下。”
“这他妈咋坚持啊?”
“唉呀,”梁续无奈的冲吴越挤眉弄眼半天,而后警觉的伸着脖子往后看了看,故作官腔的说道:
“那个,Sunny啊,有啥需要的你就和小吴说哈,我先走了,天亮就回来。”
吴越在他出门后,将钥匙藏在自己外套兜里。回身去看那床,厚厚的尘土只恶心的他气儿不打一处来。早知会有这么麻烦,自己定不会大老远的来当替罪羊。
好在,自己已经想好了对策。不多时长途跋涉的疲倦便席卷而来,他手机揣在兜里,枕着胳膊闭上了眼睛。
半梦半醒之间,耳边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吴越本来胆子就不大,一轱辘便坐了起来,低头四下找耗子。却只发现一双脚,踩在一双破旧的胶皮拖鞋上。
抬起头,月光从没有窗帘的窗户里照进来,温柔的将眼前挡住视线的身体,笼上了一层银边儿。
Sunny似乎刚洗完澡,盘起的头发还在滴着水,身上只围着一条旧毛巾。
“哥,”Sunny自顾自的在床边坐下,声音在这一片空旷中显得有些悲切。
“哥,我知道你们看出来了。”她的眼神缓缓低垂,语气越发恳切,“你帮帮我吧,我什么都愿意做。”
不知是有意无意,那眼神慢慢低到了吴越□□的位置。
吴越只感觉血把嗓子眼堵死了,脑袋嗡嗡的,他自认还没当上什么“大官儿”,没想到这“糖衣炮弹”来的这么早。
好在,进入“领导层”工作之后,吴越接触过太多姑娘。
那些“职业的”风月女子,几年之后都会回到自己的老家,有的甚至有孩子在等待着她们。她们身上带着并不高级的小纹身,穿着雪白的大衣开着车回乡之后,都能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轨迹之中。她们会将在脚踝上缠着的红绳解下来,再一次留起长发,几年之后便与在桔梗垛子旁聊闲的女人看不出差别。
女人是男人的学校,而这些女人则是男人的课外班,课外班上多了,便不会轻易被广告忽悠,甚至达到“红颜白骨”的境界。
“你把衣服穿上,”吴越清了清嗓子,强行将视线拧向别处。
“否则我现在就报警。”
事已至此,觉是睡不着了,吴越点起一根烟,在十几平米不到的“客厅”里坐好,准备好了这一段“三堂会审玉堂春”。
不多时Sunny便出来了,她将白天的衣服套上,披散开头发,走到窗边。伸手也点燃了一根烟,而后将后背倚在墙上,斜眼静静看着外面。
秋日的晚风吹来,远处的空中依旧能看见“天通苑”三个大红字。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电影电视看的太多,她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原来北京,也就是这样。
“说说吧,”吴越将手撑在膝盖上,“怎么回事啊你?”
Sunny深深的抽了一口,将烟灰弹在窗外。
“我叫关赛男。”
Sunny的家,在黑龙江与内蒙交界的地方,一个叫作呼玛的县城。
县很大,县城却不大,大部分的人,都住在在最东头和俄罗斯交界的一边。
Sunny说她不怎么幸运,没生在那里,而是生在西边的林区之中。
林区中有两拨人,鄂温克和鄂伦春,他们文化相通,世代在这里繁衍。建国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周边那些汉民的村县与城镇,慢慢都富了起来。林区里大部分的山民,都慢慢走出去,融入其中。
Sunny家却一直没走,倒不是对大山有多依恋。只是奶奶是鄂伦春出了名儿的“萨满”,总觉得要是自己也走出去了,对神明太不恭敬。这些道理,儿子并不认同,可惜拗不过母亲的意思,只得如此。山里倒是自给自足,一家人住在撮罗子里,夏天冬天换个营地,就算这么过来了。
Sunny出生之后,起名为赛男,意思自不必说,在大山里讨生活,当然是男孩儿更方便些。待到Sunny三岁了,父母便准备再要一个。
没想到怀胎八个月的时候,出了点儿意外,从山上往县里的医院赶太不及时,大人孩子都没保住。
父亲本来就在山里憋的不轻,一气之下便走了,据说去了最南边一个沿海的城市,和那里的女人又结了婚,再也没回来过。
山里只剩下两个女人,奶奶和不懂事的她。
“其实也还好,”Sunny说,“我奶奶懂的多,她教了我好多东西,野菜,松鼠,狍子,犴,她说山里的东西,都是有神明的。人从山里拿走的,都是借,总有一天要还的。”
“这叫什么,萨满——教?”吴越有些意外。
“萨满不是教,”Sunny摇了摇头,“萨满是——一种眼睛。”
“眼睛?”
“就是——萨满是通过另一种方式看这个世界,我学得不好,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奶奶本来打算传给奶奶的,但是她说,”Sunny又点了一根烟,看着黑暗中的红点儿发着愣。
“她说她做仪式之前做了个梦,梦见一件她的萨玛西卡,哦,就是萨满穿得衣服,慢慢的飞到我的衣服上,可是没等落下,我的衣服便燃烧了起来。奶奶说,这是神明的意思,继承不了,便不往下传了吧。”
等到六岁的时候,“上面”来人了,说Sunny必须要上学。奶奶没办法,找了县里几家卖山货的店铺,让他们每天进山的时候把Sunny接上,然后搭着三轮去学校。等到有了寄宿班,便干脆让Sunny住下,周末才回家。
“我那会儿小啊,什么也不懂,还挺喜欢学校的。一开始确实也不错,他们说我是少数民族,经常围着我问这问那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叫Sunny么,其实就是当初英语老师给起的啦。说跟我的名字听着像,我就一直用到现在。可惜啊,”她抿了抿嘴唇,“熟了之后,就不一样了,现在想想,他们也挺操蛋的。”
“他们说我身上有味儿,说真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反正就是,起初几个玩儿的不错的,后来也不找我玩儿了。怎么做都是不对,怎么都是不行。慢慢的,连老师也懒得理我了。你想啊,我当时普通话都说不好,学习又能好到哪儿去。”
“我到现在还记得,每次周五的时候,我奶奶来接我。都有那么几个男孩儿,躲在学校旁边老远看着她。等到我们走过去,就突然冒出来吓我们一下,然后就笑着跑了。说真的,我挺烦他们这样的,我奶奶把我养大。我不知道他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么?难道我们不是人么?”
她的眼神中划过一丝愁绪,顿了顿,又接着说了下去:“可是后来吧,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我也不大想奶奶来接我了,”
“我觉得有点儿——是丢人么,我也不知道,总之有的时候我会带着她绕很远,等到周围没人了,再回去。”Sunny似陷入了回忆里,用手机械的揉了揉脸颊。
“等上到初中,我就更想走了,说白了,就是想离开那个鬼地方。我特烦身边而这些学生们,真的,甚至说,有点儿恨吧。我觉得他们都特幼稚,还特傲。”
“当然了,他们也烦我,你知道么,就连平常换桌子,我都抢不上个干净的。都是那些个破烂的不行的,桌板儿都磨呲了的,才轮得到我。哦,对了——”
Sunny说到这里停住了,看向吴越,表情似朋友一般,微微带着笑意。
“我跟梁续就那么认识的,那张桌子。”
“嗯?”吴越没跟上她的思路,琢磨了片刻才恍然大悟。
“呵,卧槽,哪都多少年前的了。”
“啧——”Sunny撇撇嘴,将手向后撑在窗台上,“我当时又不知道,我还以为是我们学校的呢,谁知道一张桌子,能跑这么远。”
“也是。”
“诶,你猜,中考之前,我问梁续要买答案,梁续说什么?”
“呃——”吴越努力的回忆着,只是那天酒后的事情,实在不清晰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回的是‘好好学习,别想些没有用的。’”
“哈,”吴越苦笑一声,想着这话是从梁续嘴里说出来,着实有些滑稽。
“诶你别说,我当时还真听进去了呢。有时候碰上啥事儿想不开,就和他聊聊。他说人啊,不死总有出头日,气势上不能输,一输就彻底完了。他当年学习也不好,可他敢闯敢拼,现在照样能在北京混出了名堂。”
“呃,呵呵”吴越用鼻孔轻笑一声。梁续果然是还没改装逼的毛病,估计是现实中实在装不出啥了,竟然在网上过瘾。还什么不死总有出头日,不定又是看了哪本儿武侠小说撒的癔症。
“可惜我不是学习那块料,中考还是不行——后来我就去塔河了,十六岁的时候。也不会干啥,去哪儿人都不要。当时不是流行美瞳么,我就自己淘宝上进了点儿货,在路边卖。一开始根本没人理,我就蹭人家小卖店,就是学校门口卖小礼品的那种,租人家的格子放里面卖。自己拿水彩笔写的标牌,那会儿也不知道啥标语,就写‘日韩美瞳’。”
“有的学生家长找过来,说孩子戴这美瞳眼睛不舒服。其实肯定是有的啦,这种便宜玩意儿,难免有些次品,就是有些时候,有裂的,或者有鼓包。你知道我怎么整么,我就当着人的面儿,直接把那美瞳戴自己眼睛上,明明磨的要死,还咬着牙说‘没事儿啊,姐,我带着还行啊。要不我给您换一个吧。’然后笑着眨眼睛,他们也就不找我事儿了。等到从人家家出来,我就赶紧给它抠下来扔了,然后揉半天眼睛才能缓过来。”
“诶,你知道我那会儿租那房子有多破么?都不如这儿!”Sunny说着用手往四周指了指,“就是一个小单间,然后淋浴头对着床,中间就隔着半米。每次洗澡的时候啊,我都得先把床用那个地板革的席子,给罩上。地漏也不好使,还没人喝的快呢。每次洗完了啊,拖鞋啊,塑料袋什么的,飘一地。然后我就得一遍一遍的慢慢把水往里扫,扫不动了,就坐在床上等水干,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不过我那会儿就觉得,我将来肯定行的,我一定能在城市里生活,我本来就该是属于城市的。”
吴越突然也有点儿感伤,好在发现的及时,赶忙在大脑中止住了它。
“还说说说你为什么来这儿吧。”
“就是——呃,后来感觉,钱还是不够啊,”Sunny将脚叠在一起,再次将后背贴在墙上,眼神慢慢放空。“没戏,”她将这两个字咬的很重,似乎有意的模仿城市里的强调。
“城市里的开销太大,卖过耳钉,租过夜市,可城市姑娘们吃的用的,我是一样也不敢有。后来,有个也是呼玛出来的姐姐,说马富在塔河有家KTV,平日里去陪人唱唱歌,能赚不少。”
吴越暗暗点头,没想到梁续和自己以貌取人,倒还真猜对了。
“我就去了呗,一开始挺好的,只不过那些男的动手动脚,有些不习惯。后来慢慢的就想开了,本来嘛,人的身子生出来便是暴露在外面的,被什么碰都是碰,也没有人知道,怕的什么呢。”
她说着转过身,脸上的表情却很阳光,“呵,你说,我叫赛男,我爸当初可能就想我像个男的一样。问题是男人这东西,好在哪儿呢?天天吆五喝六的,到头来为的还是□□里面那点儿事。”
吴越本想纠正下,转念想想,自己在那种地方也没少了揩油,姑娘们有些看法太正常不过了,也辩驳不了什么。
“就是有一个男的,就特逗,他一开始喝两杯之后就问我出不出,我说我不出。一般这么说完也就完了,他们就找能出的‘培养感情’去了。可这个男的也许是看不上剩下的几个,又喝了几杯之后,趁着没人唱的功夫,坐到我旁边。”
“他说,你看,我现在问你,你说你不出。可能呢,是因为,没有看上我,那无所谓——但是你看哈,你这么大,肯定也追星是吧。”
“如果我长得,和你最喜欢的男明星一样。或者说,我就是那个男明星,来你店儿里消费了,这时候就看上你了,想带你出去睡一觉,你出不出?”
“我头回听见有人这么打比方,都给我问蒙了。他又说,又或者,我是马云谁的,反正贼有钱,拍一万放这,你说你出不出?我摇摇头,他又一笔画,两万,三万,五万,十万,二十万?我就这么一点儿点儿往上加,姑娘,你说你能一直不出么?”
“呵,”吴越听见这“拉寡妇下水”的伎俩,又有几分汗颜,摇了摇头。Sunny也笑了,用手搓了搓鼻子,一时没有再说下去。
“那你跟梁续,啊不,梁老师,有没有那个——”吴越有些羞于说出那个字眼。
“没有,”Sunny摇摇头,“隔着老远呢。”
“哦哦,”吴越点点头,心中暗自踏实了一些,“就是聊天儿哈?”
“呃——说过几句吧,后来他好像也不怎么玩儿QQ了,很少见他上线。有一次我想来北京看看来着,他好几天之后才回,说来的话,有事儿找他就好了。哦对,还有一回,他啊——”Sunny突然嘴角上扬,噗嗤一乐,没有再说下去。
“怎么了?”
“没事儿,等回头,你问他吧。我可不好意思说。”
吴越点点头,暗自思忖什么话题连这姑娘都不愿意说,但也不想把话题拉太远。
“你接着说,你这趟来干什么。”
“后来我在马富店里认识一个人,他挺好的,贼老实。头几次来的时候,就是低头喝酒,也不唱歌。来三四次吧,都没碰过我,但每次还都就找我,我不在,他也不点别的姑娘。”
“跟他一块儿来的都是些老手了,看他这样总说他。有一次酒喝多了,他们就起哄,趁他不注意,拉起他的手就塞到我衣服里面。给他羞了个大红脸,蹭的一下就站起来了。”
“说真的,除了那些个偷摸来玩儿的学生,我还头回儿见到这样的。后来慢慢的就熟了,才知道他是当兵的,刚专业,给分到这里。”
Sunny说到这里,声音低了很多,努力抿了抿嘴唇,才又说下去。
“再后来,我俩就在一起了,我把我奶奶那块地卖给了马富,结了婚。可结完婚,那个男人也跑了。他说是去外地出差,慢慢就不怎么回来了。我那段时间真挺难受的,也不敢在家耗着,没钱,只能再回去上班。”
“去年马富的儿子开始来店里玩儿,他可能是知道他们家帮过我,就故意折腾。”
“折腾?”
“就是——每次去都偏要找我。我本来是四百台的,他点的都是三百台的,却偏偏要把我带上。”
“嗯?”吴越有点儿没明白其中含义。
Sunny咬了咬嘴唇,有些迟疑,用手揉了揉脖子。
“我们那儿的三百台,进屋便要把上衣脱了的。”
吴越有些后悔问出这问题,轻轻嗯了一声,将头低下。
“他那一堆人都没我岁数大,我挺不乐意的,就躲着不见。后来又被他撞见一回,把我拉屋里了。我去的时候,他和那些十几岁的孩子早就喝的东倒西歪,见我进来便是一阵起哄。那能怎么整啊,陪着喝呗。那天马清源也多了,还说什么让我跟着他,说我那老公就是个骗子。”
“是,我活的没他们体面,我命不好,我倒霉。可我也不想被个十几岁的孩子戳着脊梁骨笑话。也是喝多了点儿,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拿起个酒瓶,把马富的儿子给开了。”
“呵——”吴越听到这,突觉得有一丝解气。也庆幸,自己并没有挨上两下。
“那之后我就跑了,跑到我们那另一家KTV里躲了起来。那家KTV的老板人比较好,告诉我说我那块地卖亏了,政府在山上有项目,马富就是靠着倒手了那块地,赚了几百万。”
她叹了口气,“我这才明白,怪不得当初马富答应的那么脆,感情是算计好了。他明明就知道,却还要我在他手底下干这个。我就气不过这个理,这钱哪怕有我一半儿,我也不会是现在这样。我去找他要钱,马富自然是不认账的。我就说他这是诈骗,是犯法,说要闹到北京来——”
Sunny说至此处,天已全然亮了起来,城中村里,竟然也传来了几声鸡叫。
吴越瞪红了眼睛,打了个哈欠。
“那你来了,能咋办?”
“我也不知道,”Sunny深吸了一口气,缓缓伴着烟气吹散在窗外。她好久没给人讲过她的故事,心里当真松快了很多。
“吴哥,你们能帮我的对么?”
“呃——”吴越有些迟疑。
“哥,你知道么,来这儿太不容易了。我本来都到了火车站了,临要上车的时候,突然来了四个学生,愣是给我围在座位上了。我怎么钻,怎么说,他们都不让开。我认识他们,平日里都是跟着马清源的。我最后没办法了,四处喊,说他们围住我不让我走,可没有人过来帮我。我也不知道几个十几岁的孩子,怎么心就那么狠,我就差给他们跪下了。我眼睁睁看着那辆车从我眼前开走,那会儿我真想他妈跳下去。”
“嗯——”吴越用鼻子长长呼出一口气,胳膊撑在膝盖上,有些酸痛。“你们当初有合同么?”
Sunny凝视着远处的阳光,无奈的摇了摇头。“就签了个字,我也没想那么多,拿着钱就走了。”
“你这——”吴越苦笑一声,这倒也无法苛责,一个初中毕业的小姑娘,哪懂得这里面的弯弯绕。况且说到底,这事儿她也不占理,只是有些贪心罢了。
“那演唱会呢?”吴越想起白天的事情,“你——是故意到那熊窝里去的吧,为什么?”
“呃——”Sunny有点儿不好意思,“我想要一点儿,呃,熊的血。”
“熊的血?”
“嗯,我奶奶当初教我的,说这个林子里面,熊是最厉害的。谁要是能弄来熊的血,神明就会向着他。”
“哈,”吴越摇了摇头,这才明白了事情原委。他见过太多来北京“找事儿”的,似Sunny这般,未免太异想天开了。
“证明证明没有,合同合同没有。这些你不想办法,来了先找熊较劲,怎么,你奶奶比法律还靠谱?”
Sunny突然转过头,看着吴越,“哥,你们他能帮我的,对么?”她脸上的笑容似有意练习过般,晴朗又带着一丝可怜。
“呃——”吴越揉了揉已经肿胀的眼睛,心中日了梁续的祖宗十八遍。
但无论如何,还是不能感情用事。吴越抬起头,看着那块斑驳的天花板,将早想好的理由道出:
“你其实应该早点儿说的。”
Sunny看着远处的太阳,突然有些感慨:
“其实——我都没想好说不说。虽然我也没别的办法,但总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
吴越略感错愕,“呃?你不就是来办这个的么”。
“——对啊,可是——你说,他教了我那么多道理,我还是没把日子过好,是不是有点儿——丢人。哈,丢人,”她说到这里突然轻轻笑了,“小吴哥,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刚才那样,特下贱?”
“呃——”吴越没想到她会这么□□裸的说,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无所谓啦,”Sunny转回头,“我就是,不想让续哥太失望。”
“你应该也见过不少我这样的吧,可能觉得这种姑娘,不该再要什么脸。其实不是,你看我在场子里见过那么多人,我就觉得吧,人这东西,特奇怪。”
“没人天生爱撒谎,可越是混的不济,越强撑着让脸上好看一点。那些每天劲儿劲儿的,吆五喝六的人啊,不都是怕被人看扁了么。我也想像这儿的姑娘们似的,和你们聊电影,喝咖啡,拍照片,可这些,我也不成啊。”
“本来嘛,即便我不撒谎,你们也看不起我的,你说是吧。那我就做个脸呗,起码自己心里舒服点儿。我跟你说哥,只要那脸上干净了,光鲜了,身子被踩在泥里也无所谓的,即便挨了打,都不觉得痛了。”
Sunny说完,用力的伸了个懒腰,阳光透过她身体的缝隙,洒进屋子,似乎一切都是有希望的模样。
楼下的角落里,一根烟头在地上被踩灭。
似乎是第一次,听一个女人讲自己的人生。东子抬起手,用掌心揉了揉酸痛的眼睛。
他想,这女人,本就该是自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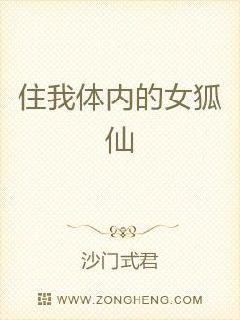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