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绝塞》最新免费章节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二章
1976年10月,时隔三十年,周太暄夫妇带着小儿子回到故乡。
很多当年的同志纷纷来看望周太暄,最勤的是汤菊中。他已经七十七岁了,圆圆的大脑袋已经没有头发,身板仍然硬朗,走起路来还很有力,嗓音虽有些沙哑,中气很足。他咋眼一看是个很不起眼儿老头,只有在讲话的时候,仍能感觉到他浑身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力量和冲动。
三十年前一别,如今已是物是人非,看到当年风华正茂英俊潇洒的周太暄如此苍老病弱,汤菊中不禁老泪纵横。老友相见相互问了一些别后发生的事情。
周太暄离开湖南后,汤菊中受省工委和省军事策反小组的派遣,冒着生命危险,成功策动国民党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所部师长杨光耀起义。起义后,杨光耀所部交与解放军47军曹里怀部接收改编。
解放后,汤菊中当过长沙教育局长,后因立场问题,降职降级,安排到铁路局附属学校做了一名校长。
周太暄非常想见当年一起策反韩梅村的邓洪夫妇,很多人劝周太暄,说邓洪犯了错误,还是不要接触为好。周太暄不听劝告,打听到邓洪住在岳麓山,就带着妻子和儿子去拜访邓洪一家。
他们坐公交车到了河西。下车后周太暄吃力地往邓洪家走,他每走几分钟就要停下来休息,走了大约过一个小时才到岳麓山脚下。
邓家在半山坡,上坡路周太暄走起来更加困难,儿子搀着他一歩一步来到半山坡,这里有一排红砖平房,邓洪家应该就在这里。
房子的四周山林茂密,环境阴凉幽静。房子墙体已经发黑,长了藓苔。房前有几个女人在闲聊,看到有人来,他们好奇地问找谁,听说是找邓洪的,一个女人往前指了指说,应该是靠最西面的那扇门。
来到门前,周太暄轻轻地敲了几下。门开了,开门的是邓洪的妻子李茵,邓洪紧跟在李茵的身后。
“老邓、李茵,你们好啊!”看到邓洪夫妇,周太暄兴奋地打招呼。
邓洪夫妇显然没有认出周太暄夫妇,李茵迟疑地问道:“你们是哪个?”
“我是周太暄啊,这是陶杏生啊!”
“是太暄来了!”邓洪激动地冲过来握住周太暄的手,“老了,认不得了!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接着,邓洪夫妇把周太暄一家让到卧室。邓家只有两间房子,邓洪住一间,他的大儿子晓芒和小儿子眯子住另一间,妻子李茵带大女儿小妹和小女儿小华住在报社的宿舍。
周太暄夫妇和邓洪夫妇1947年共同策动了韩梅村部的起义。起义胜利后邓洪夫妇回到老家,邓洪在报社任总编,后来撤了职,一直赋闲在家。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两对夫妇经历了人生的辉煌,也经历了苦难的磨砺,眼见着已经进入暮年。老友相见百感交集,他们的话题从韩梅村开始。
周太暄问邓洪:“不知道韩梅村在不在了?如果他还活着,应该快八十岁了。”
邓洪摇了摇头:“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我这些年几乎与世隔绝,听说他解放后在江西什么地方作了军分区的司令员,后来又当了农垦厅副厅长,不知这十年文化大革命他能不能平安度过去。”
周太暄感叹道:“韩梅村这个人不简单。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在东北占有优势,他身居高位,又是杜聿明的亲信,老婆孩子七八口人,能舍掉一切跟着共产党走,为了理想他真是不顾一切!”
邓洪点点头:“推翻腐败独裁的国民党,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是我们,还有像韩梅村那样一批追求进步人士的必然选择,在当时那个历史环境下,共产党是我们这些人的共同选择,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与国民党那批贪官污吏们为伍的!”
周太暄说:“是的,我们非常清楚要打破一个旧世界......”
接下来的日子,两家人走动很勤。李茵住的比较近,经常带着女儿来看周太暄一家,有时她还特地做了粉蒸肉送了过来。李茵是童养媳出身,看起来很温和,其实她的性格非常刚烈。
邓洪的小女儿小华也经常来看周太暄一家。一次,周太暄的朋友请吃饭,正好小华也在,周太暄就请小华跟着一起去。她大大方方地同意了。那天,她身穿一件薄棉袄,上面有四五处补丁,路人都盯着她身上的补丁看,而她却满不在乎,有说有笑旁若无人。小华二十三四岁,脸上常挂着淡淡的笑容,有一种出水芙蓉般的美。
小华梦想成为作家,但她接触的人很少,她大多数的时间是神游于书籍和自己的世界。周太暄一家的出现,给她一个观察社会的机会,她很好奇,她在观察和想象周太暄一家人,在脑海中编排着有关周太暄一家的故事。
周太暄知道小华在试着写小说,就让她拿几本过来欣赏一下。过了几天,小华带来一本她写的童话,一个类似美人鱼的故事,写得很美,但有模仿安徒生的痕迹。又过了几个月,她又带来一篇新作,叫《泥街》。里面写了很多肮脏的东西,比如浓痰,她写的很细。对于“泥街”的描写也很灰暗,很压抑。
周太暄对邓洪的大儿子晓芒很感兴趣,两人经常谈一些哲学方面的问题。晓芒靠拖板车为生,拖板车虽然耗费体力,但工作时间短,可以读书。很快周太暄和晓芒成了忘年交。晓芒特还让周太暄参加了他搞的讨论会,地点就在他家报社的宿舍。那天来了二十多个和晓芒年龄差不多的青年,其中有知青、工人、自由职业者,这些都是同晓芒一样,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对诸如文学、哲学、美学、绘画、历史有很深的研究。
周太暄同年轻人们一起讨论着,他们的话题从哲学、历史,渐渐地转到对前途命运的思考。周太暄好像变了一个人,他忘记了病痛,仿佛又回到二十几岁的青年时代,他慷慨激昂,热情像一团火在他眼睛里燃烧。
周鼎勋此时任职邵阳地委副书记兼冷水江市委书记。他虽然在冷水江工作,但家还在长沙。他在长沙住在芙蓉宾馆,每次回来,都要把哥哥周太暄接到芙蓉宾馆洗澡,跟他分享一下贵宾待遇。
为解哥哥思乡之苦,周鼎勋特地陪哥哥一家三口回宁乡。县领导对周家兄弟非常热情,他们设宴款待这两位从本县出去的大人物。
宴会在机关招待所的单间进行。机关招待所虽然装修朴素,但食物非常丰盛,鸡鸭鱼肉满满的一大桌子。盛菜的容器都比较大,鱼肉都装在陶制的大钵子里,有红烧大鲤鱼、炖整鸡、蒸肘子和红烧甲鱼。
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出面接待,酒席之间,大家天南海北谈得很高兴。这次宴请,一方面是欢迎周太暄这位远方游子归来,更主要还是看周鼎勋的面子,周鼎勋曾是县里的老领导,现在仍居高位,其德高望重,前途未可限量。
周太暄回到家乡,当年的学生们都很高兴,在长沙的学生相约请周太暄吃一餐饭,学生刘美主动要求操办。刘美现在是省招待所的所长,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那天晚上,刘美派车接了周太暄一家。车子开进一个有卫兵把守的院子,院子很大,很寂静,昏暗中只有点点光亮。
车在一栋平房前停下,周太暄等人刚下车,一个短发圆脸,显得很干练的中年女性迎了上来。
“刘美。”周太暄一眼就认出了她。
刘美迎上来握住周太暄的手,激动地喊了一声“周老师!”
她上下打量着老师,老师的苍老显然出乎想象,泪水不禁从刘美眼里夺眶而出,她小心地扶着老师往里走。
周太暄走几步就气喘吁吁,他停住脚步,剧烈地咳嗽起来。刘美一手搀着老师,另一手轻轻地拍打着老师的后背。
走进餐厅,只有角落里点着一盏汽灯,诺大的餐厅显得有些幽暗。周太暄一行走到点着汽灯的角落,那里被屏风围了起来。绕过屏风,里面摆着一张巨大的餐桌,还有十几个人。看到周太暄进来,里面的人马上围了过来,热情地和周太暄握手,他们大多是周太暄的学生,肖强、庞诚也来了。
同学们虽然早就听说周老师的身体不好,但亲眼见到老师的状况,还是感到非常痛心。大家关切地询问老师的病情和致病的原因,大家听了老师这些年的遭遇,都不禁为老师难过和不平。
周太暄也很关心同学们的近况,他们都是处局级干部,这些年应该都没少遭罪。
周太暄问:“彭梅怎么没来?”
大家都沉默了。
看着老师疑惑的目光,肖强打破了沉默:“是我们不想让她来。”
周太暄更觉得奇怪:“为什么呢?”
肖强稍微迟疑了一下回答:“彭梅已经不是你当年认识的那个彭梅了,她们两口子整了不少人,邓洪夫妇就是她整的。”
听了肖强的话,周太暄陷入了沉思,他脑海里浮现出彭梅当年那张纯真热情的面孔。他想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将当年的那个追求自由、天真热情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整人的人。
“来,周老师,各位同学,我们开始吃饭吧!”刘美的声音让周太暄回到了现实。
这时酒菜已经上齐了,摆了满满一桌,仍旧是用大钵子装整鸡、整肘子、整条鱼、甲鱼等等,菜比上次宁乡之行丰盛得多。
看着一大桌子菜,周太暄向刘美道谢:“刘美,搞这么多菜,让你破费啦!”
庞诚笑着说:“周老师,到了这里您就不用担心了,刘美是这里的大所长,别说是老师您来,平时就是我们来,也得由她招待。”
“你们都是处长,局长,我刘美就是一个小小的招待所长,能荣幸地为老师同学们服务真的是我最高兴的事。”
周太暄皱起眉头,显然有些不高兴,他刚要开口,陶杏生在旁边拽了一下丈夫的衣袖,周太暄明白妻子是不想扫了大家的兴,他叹了口气,低头不语。
席间学生们七嘴八舌地回忆起当年周老师对他们的关心和教育,纷纷说如果不是周老师,他们不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刘美有些激动,起身敬老师酒,周太暄刚要起身,刘美赶忙过来按住老师:“这杯酒是我对老师的衷心感谢和祝福,我干了,老师随意。”
说着她把杯中酒一饮而尽。周太暄慈祥地望着刘美,也喝干了自己杯中的酒,刘美笑着夹起一块甲鱼腿放到老师碗里。
接着同学们依次向老师敬酒,周太暄高兴,也喝了不少。
酒过三巡,大家的话题又回到了当年,周太暄突然问道:“彭卓夫老师怎么样了?当年他对你们最关心,照顾最多。你们记不记得他当年收留张昱的事?如果不是卓夫老师,张昱这个流浪儿不知能不能活下来。”
听到彭卓夫的名字,气氛好像有些紧张,大家对视一下,谁也没有作声。
周太暄追问:“卓夫老师现在怎么样了?”
刘美打圆场:“我们之间很少联系,刚解放时他当过民政局局长,解放初期好像就犯了错误,现在好像还在乡下种田。”
听到彭卓夫的消息,周太暄黯然神伤,他眉头紧蹙,目光移向远方,许久才回过神来。周太暄沉重地说:“卓夫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一家为了革命牺牲了好几口人。你们这些同学,包括我本人,都是跟着他们那一辈人才懂了革命的道理。”
周太暄说完,席间一片沉默。
晚餐快结束时,刘美对周太暄说:“老师,张昱想请您到她家里吃餐饭。”
“好啊。”周太暄想见见张昱,一晃都三十年没见了,当年他们收留的那个流**孩如今不知变成什么样了。
其他学生一听张昱要请老师到家里吃饭都很高兴,张昱现在可是省里的第一夫人,她丈夫是党政一把手,现在别说让她请,就是能请得动她的人都不多了。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一个头发梳的很亮,穿着一身绿军装,身材富态的中年女人来接周太暄夫妇到她家吃饭,她就是张昱。
晚餐的时间不长,张昱同志让司机把周太暄夫妇送了回来。
一直闷声不语的陶杏生埋怨丈夫:“太暄,大家好不容易见一面,你不该又提彭卓夫。”
周太暄很激动:“我就是要提,人不能忘本,当年不是彭卓夫,她张昱能不能活到今天都是问题!”
陶杏生也有些生气,她顶了一句:“你这样搞,最后迟早成孤家寡人。”
周太暄怒气冲冲地回了一句:“孤家寡人就孤家寡人,我是舍得一身剐。”
接着,周太暄剧烈的咳嗽起来。
早上醒来,周太暄把儿子周铁肩叫过去,让他到长途汽车站买两张到老家的车票,明天陪他一起去老家看看彭卓夫。
第二天一早,陶杏生照例出去买菜,周太暄父子直奔长途汽车站,登上了前往老家的长途汽车。
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来到县城。下了车,周太暄拿着准备好的地址,他们边走边问路。一会儿,他们就走出县城,来到乡间小路,周太暄走三五十米就要歇一下,他准备了折叠小凳子,累了就找个树荫下喘口气。
大约又走了半个多小时,他们问过路的老农,那老农听说是找彭卓夫的,自告奋勇带路。
没有多久,他们来到一个小山坳。山上长满了茂密的竹子,山坳湾里有一栋茅草屋,草屋前有一汪水塘,老农手指着那茅屋说:“那个屋就是了。”
周太暄谢过老农,加快了脚步,气喘吁吁地赶过去。
来到门口,门大开着,灶屋里没有人,周太暄急切地喊着:“老彭,老彭,彭卓夫同志!”
没有人回应,但听得屋子里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一会儿,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颤颤巍巍地走出来。
周太暄迎上去:“你是大嫂吧?卓夫在家吗?”
老太太上下打量着周太暄父子,疑惑地问:“你是哪个?”
周太暄说:“我是周太暄,告诉老彭,太暄来看他了!”
老太太是彭卓夫后老伴,他的原配被国民党抓起来杀掉了,这个后老伴是个地道的农民,一直跟着彭卓夫,,风风雨雨地陪伴着。
这时一个老人从屋里出来,周太暄一眼就认出他来:“卓夫,卓夫同志!”
周太暄激动地紧紧地握住彭卓夫的手,彭卓夫愣住了。
彭卓夫有八十多岁,个子比周太暄高,黑瘦黑瘦的,但很结实,完完全全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庄稼汉,那双深邃的眼睛还闪着炽热的光。
周太暄急切地对他说:“老彭,不认识我了,我是周太暄呀!”
“你是太暄,周太暄?”彭卓夫注视着周太暄,仿佛穿透岁月在寻找当年的影子,看着看着,彭卓夫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他摇了摇头:“认不出了,变了,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了?”
周太暄眼里也饱含着泪水:“卓夫同志,你也老了,不过神气还是老样子。”
彭卓夫拉着周太暄的手走进了屋子。屋子不大,有一张很旧的牙床,白蚊帐快成黑色了,窗前有一张黑色的木桌子,两把藤椅,一张竹床,还有一个竹茶几。
周太暄发现彭卓夫的耳朵不好,必须大声喊他才能听见,他问:“老彭,你的耳朵出了什么问题?”
彭卓夫不想说,在周太暄坚持下他才道出原委。若干年前,北方来了两个人,让彭卓夫写材料陷害周太暄,被他拒绝,那两个人恼羞成怒竟殴打老人,老人的耳朵就是那次被打坏了。
周太暄默默地听着,他心情异常沉重,仿佛有一块铅堵在心里,让他喘不上气来。
正午的阳光穿过土墙上的破窗照进来,在黑暗的屋内形成了一束炫目的光柱,光柱的两边的黑影里,周太暄和左夫像两尊塑像一动不动,他们的思绪飞回到三四十年前。
“后悔么?”彭卓夫慈祥地望着周太暄轻声地问。
周太暄微微摇头,凝望着老朋友,当年的镜头一幕幕地在眼前浮现。那时自己还是八九岁的孩子,失去了父亲,母亲改嫁,一个人被寄宿在学校。彭卓夫经常到学校看望自己,给自己带来生活费、一些衣物,还带来许多书籍,给自己讲革命道理。特别是1941年9年,他介绍到自己到思三学校做教师,他们以教书为掩护,帮助教育进步学生,在学生们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
周太暄说:“即使再来一次,我的选择还会是这样。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出生的那个时代,中国正经历着三千年来未曾有过的大变局,我们整个民族都在寻找自己的路,每个人也在寻找人生的希望。我们的斗争没有错,不斗争中国就没有新生的可能,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民族来到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交叉的历史关口,没几百年的斗争,我们走不出迷途。但我相信我们这个民族会走向光明,我自始至终有这个信心。”
一阵剧烈的咳嗽中断了周太暄的谈话,他痛苦地咳着,喘不过气来,脸憋得通红。周铁肩走过去,轻轻地拍打着父亲的后背。
彭卓夫端来一杯茶,难过地看着周太暄:“太暄,你身体不好,要少讲话。”
“我的身体不行了,我现在越来越能够体会陆放翁晚年的心境,”周太暄的目光慢慢远去,他低声吟诵起陆游的诗句,“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彭卓夫沉重地点点头,他安慰周太暄:“太暄,不要着急,历史有它自己的规律,对于历史来讲,几百年算不了什么。”
他们二人陷入了沉思。
忽然,彭卓夫好像想起了什么,眼睛一亮:“太暄,还记得我第一次教你唱《国际歌》的情景么?那时候你还是个孩子。”
周太暄深情地望着彭卓夫点点头,他轻声地唱起来,彭卓夫也随着小声地唱起来,越唱越激动,两位老人不禁老泪纵横:
“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太阳向西方偏去,光芒渐渐移出了小屋,室内昏暗起来。两位老人还沉醉在内心的辉煌之中,理想的火焰仍然在胸中熊熊燃烧,整个小屋仿佛充满了激情和光明。
周铁肩默默地走了出去,彭卓夫老伴一个人坐在灶膛前,右肘撑在膝盖上,手掌托着腮帮,静静地听着从屋子里传来的歌声。灶膛中的火光映红了她苍老的面庞,她看着周铁肩,微微点头笑了一下,目光又随着歌声远去。
周铁肩走出房门,门前池塘里的水是那样平静,山影倒映在水中,仿佛是一幅画。他信步向后山走去,各种不知名的鸟儿在叽叽喳喳叫着,非常好听。暖风轻抚,竹林摇动,绿色连成一片,从山上延伸到稻田,再向远处铺过去,在最遥远处,绿色和蓝天融合到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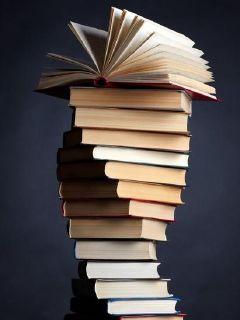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