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唐记》最新免费章节十一、飞龙再现
十一、飞龙再现
话说城西大寨劳军朱延寿与严泰针锋相对,但偌大个扬州城依然太平祥和。一家酒馆内热闹非凡,十多个人聚在酒桌前,或站或坐或一脚踩着椅子。这其中一人如同吃了败仗,唉声叹气道:“他奶奶的!今天这是什么鬼运气,从早到晚一把没赢过,输了个丁二咣当响,不玩了不玩了,再玩老子饭都没着落了。”另一人嘲笑道:“我说肖飞,你玩不玩得起,赌博各凭运气,别再那怨天尤人的,没钱了闪到一边去,还有其他人等着玩,别耽误我们赚钱。”旁边众人起哄道:“就是,没钱了赶紧走。”肖飞悻悻地将脚从椅子上挪下,收拾了座上仅剩的几个铜板,欲离开酒馆。
这时,一人拍了拍肖飞肩膀,说道:“小兄弟,我帮你如何?”肖飞转过身来,见一方面大耳、硕大无朋的胖子,这胖子五十岁上下,打扮华丽,头戴鹘衔瑞草浑脱帽,身着孔雀绫翻领长袍,腰系真珠宝绶带,悬挂瑜玉双佩,下着长裤,足登乌皮六合靴,五指带满玉戒指,手拿一个金算盘。肖飞十分好奇道:“阁下准备如何帮我?”胖子笑道:“自然是帮你赢了。”肖飞问道:“人都说赌博全凭运气,看得是天意,难道阁下还能看透天意不成?”胖子笑道:“那是自然!”肖飞若听得其他人说起此话,定然认为是些疯语,但见此人穿着不简单,心知这胖子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便更加好奇问道:“阁下准备如何看透这天意?”胖子说道:“你那身上的铜钱借我使使。”
肖飞将信将疑将怀中的仅剩的铜钱掏了出来,递给了胖子,不多不少正好三枚。胖子拿着三枚铜钱,走到一个酒桌旁坐下,从怀中掏出一个甲鱼壳,将三枚硬币装入甲鱼壳内。肖飞不知所谓,摇头道:“这是干什么?”胖子说道:“这自然是窥测天意。”肖飞伸手欲抢回自己的铜钱,说道:“你这胖子欺我肖飞没见识,我们都是摇签,哪有用铜钱测天意的?”酒馆的账房在一旁说道:“不是欺你没见识,你是真的没见识,这是算卦!”肖飞对着账房翻了一个白眼。
胖子拿着甲鱼壳,并没有还肖飞三枚铜钱的意思,而是说道:“你拿出一两银子来做本钱,这回我帮你把之前的输掉的全部赢回来如何?”肖飞面露难色,说道:“我刚刚把身上的银子全部输了出去,现在仅剩下这三枚铜钱了,哪里拿得出一两银子本钱?”胖子盯着肖飞,冷冷地说道:“你怀里不是还揣着一两银子吗?不多不少正好可当本钱。”肖飞听了此话,暗自奇道:“这人难道是天下的大罗神仙下凡,也真是神了,他如何知道我身上还有一两银子?”肖飞满脸疑惑地看着胖子,不敢再有不敬,说道:“阁下真是神人!只是这一两银子是留着娶婆娘的,万万不敢拿出来。”胖子不屑地说道:“你这一两银子如是输了,我全额赔给你,只需要你暂时拿出来作为赌本,如是赢了本钱还是你的,但赢得钱财得分我一半。”肖飞心中揣着这事稳赚不赔的买卖,便从怀中摸索了半晌,掏出了一两银子放在了桌上,目不转睛地看着胖子。
胖子叫道:“小二,上碗水来。”一个店小二用一个青瓷碗装了水,放到了桌前。胖子拿着甲鱼壳摇晃了几下,听得铜钱在甲鱼壳内“叮咚”作响,然后将铜钱倒在了酒桌之上。只见,三枚铜钱外圆内方,在桌上翻转落定,一枚铜钱正面朝上,铜绿间露出“开元通宝”四个字,其余两枚皆背面朝上。胖子看着桌上的铜钱,用手蘸了些水,在桌上画了两个断横,接着又将铜钱装入内甲鱼壳摇晃起来,如此往复六次,皆是一枚铜钱正面朝上,剩余两枚背面朝上。
胖子看了看桌子上水迹未干的卦象,低头说道:“坤卦!”肖飞悔恨道:“困卦?那不是说我今日要困顿了,这钱还是不赌了。”胖子笑着说道:“此坤卦非彼困卦。坤乃万物之母,正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伏羲将坤卦排六十四卦之首,这是再好不过的卦象。”肖飞不信道:“既然是非常好的卦,为何我前面输的这么惨?”胖子不紧不慢地说道:“坤卦六一中说道:‘履霜,坚冰至’,正和你之前征兆,正所谓‘冰冻三尺,万物归藏’,如此情况你如何赢得了?只是这坤卦六三之数乃是‘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或从王事’恰好暗指今日你我相遇,只要你按我所说,保你渡过六三之数,直上上爻,到时赢回本钱自然不是什么难事。”肖飞听得云里雾里,挠了挠头说道:“阁下学问高深,咱且不管它是什么狗屁煎饼还是什么上窑,只要能赢钱就行。”胖子笑道:“话糙理不糙。”肖飞问道:“高人,我这一两银子该压什么呢?”胖子将五个手指在胸前拨棱了几下,说道:“坤卦乃是臣道、妻道,讲究和顺舒展,你就压围骰。”肖飞听了一愣,说道:“压围骰?围骰十把出不了一把。”胖子擦了擦手中的甲鱼壳,说道:“就压围骰。”肖飞心中犹豫,拿着一两银子举棋不定。
赌博众人等得不耐烦,起哄道:“我说肖飞啊,你到底玩不玩?不玩别耽误我赚钱。”“肖飞,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一个人拿了个鸟乌龟壳,算卦也没个道士模样,说着不着边际的话,你就信他压围骰?到时折了老婆本可别哭爹喊娘。”“就是,肖飞,你可下注的时候看好这人,到时跑了可没人赔你了。 ”肖飞骂道:“你们这些丧良心的知道个屁!”说罢,便不再犹豫,狠心将自己的银子全部压在了围骰之上。荷官拿起骰盅喊道:“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六个骰子滴流乱转,众人眼睛死死盯着荷官手中骰盅,目光没有丝毫偏移,肖飞却无心在赌桌上,时不时转身瞄着胖子,生怕人跑了。荷官将摇了几下的骰子放在桌上,说道:“开!”众人一看,皆大吃一惊道:“奇了,竟真是围骰!”
肖飞看了先是一愣,后缓过神来,将桌上堆着的银子都扫到桌角,支起自己的袍子将银两撞了个满怀,笑地合不拢嘴道:“我肖飞时来运转,哈哈哈,这次发了。”
胖子走上前去,拍了拍肖飞肩膀伸出手道:“说好的规矩呢?”肖飞装傻充楞道:“什么规矩?”胖子伸出五指狠狠掐住肖飞左腕,冷笑道:“你真不知道?”肖飞吃痛不住,求饶道:“贵人饶了小人,小人想起来了,这银子要分贵人一半。”胖子松开手腕,肖飞如释重负,一手牵着袍子,一手伸至嘴边吹着五指印痕。肖飞心知这胖子不是善茬,无法任意欺辱,只得极不情愿将袍中的银两清点了,对半分给了胖子。
胖子拿出一个玄布袋子,将银两统统装入其中,扎牢了袋口,提着要走,门口走进一个士卒模样的人挡住了去路。这士卒见了胖子,拱手道:“军师,我有要事禀告。”胖子招了招手,士卒走上前在胖子耳边低声细语了几句,胖子脸色一变,大叫道:“这是何等的昏聩,才会做出这种事情?竖子不足与谋,竖子不足与谋!”说罢,与士卒急急离开了酒馆。肖飞见此又是一奇,便向账房问道:“这人处处透着意外,你认得这人吗?这是什么人?”账房嘲笑道:“瞎了你的一双招子,连大名鼎鼎的钱威一都不认识了?”众人惊道:“原来他就是‘天机神算’ 钱威一啊,怪不得能算出这把是围骰。”肖飞对地啐了一口唾沫道:“这钱威一在朱延寿手下当军师,钱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竟还和我这种人争几两银子,真是掉钱眼了。”说罢,抱着自己的银两也离开了酒馆。
钱威一匆匆赶到了金谷园内院,见朱延寿正和王总管正在喝酒,二人满脸写着得意。钱威一走进主厅,朱延寿见到钱威一连忙招呼道:“钱兄来了,赶紧就坐,咱们喝一杯。”钱威一在右侧就坐,侍女上来了精准小菜和碗筷,钱威一不动声色地问道:“不知今天朱大人因何事如此高兴?”朱延寿洋洋得意地说道:“你有所不知,今天我们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钱威一故作不知,问道:“除掉心腹大患?还请朱大人详细讲述一二。”朱延寿正准备说,却被一旁的王总管抢先说道:“今日,杨行密来我们朱大人的城西大寨劳军,朱大人命令副将不开寨门,惹得杨行密前驱生气不过,在寨门前动起武来,借此机会引出安仁义,并找来一个人假作朱温密使,托了一个书法圣手模仿安仁义笔迹,伪造了一封与朱温暗自勾连的书信,做实了安仁义通敌卖国的罪证,中间虽窜出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子,差点坏了朱大人大事,但幸好证据确凿,如今安仁义已被关入刑部大牢,城东大寨再也不是你我心中隐患。”说完,王总管拿着酒杯走到钱威一面前,说道:“钱兄觉得我这计谋如何?哈哈哈,为今日除掉眼中钉肉中刺,咱干一杯。”
钱威一坐在座位之上没有起身,也不端杯子,只是闷着头吃着小菜。王总管见钱威一不理睬,只得悻悻地回到自己座前坐下。朱延寿见气氛有些尴尬,便也端起酒杯走到钱威一面前,说道:“今日如此高兴之事,钱兄身为我的军师怎么能不喝一杯?”钱威一依然不端杯子,而是说道:“朱大人,我实在不知今日有何高兴值得痛饮。大人难道已经安稳坐上了吴王的宝座?如是朱大人已经安稳坐上了这吴王宝座,今日别说痛饮,就是喝死我钱威一也是心甘的。”朱延寿见钱威一如此不识抬举,面露不悦之色,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钱威一吃了几口小菜,缓缓走出桌前,跪在朱延寿面前,禀告道:“朱大人,我有一事要禀告。”朱延寿看着钱威一冷冷地说道:“钱兄刚才姿态摆的如此高,现在为何又是如此?”钱威一说道:“刚刚在桌前,您是主,我是客,主随客便,现在您是君,我是臣,自然要行礼。”朱延寿脸色稍有缓和,说道:“钱兄不必在意如此细节,事情明日再商议也不迟,咱先吃酒。”钱威一跪着并不起身,说道:“朱大人,此事十分重要,你且听我一说……”钱威一正想着往下说,却被朱延寿打断道:“钱兄终日受案牍劳形之苦,今日就暂且放下公事,好好放松一下,切莫让公事扰了你我雅兴。”钱威一说道:“今日之事不说,我怕朱大人别说吴王,就是现在荣华富贵也很难保住。”朱延寿听了一惊,正襟危坐地说道:“如此严重?你且说来听听。”
钱威一说道:“今日城西大寨之事实在太过拙劣,恐为朱大人引来杀身之祸。”王总管坐不住,站起身来说道:“钱威一,你这话说的,难道我费心费力为朱大人出谋划策,还是有心害朱大人不成?”钱威一看了一眼王总管,冷笑道:“我道是谁为朱大人出了计谋竟如此拙劣,原来是王总管,这就不稀奇了。”王总管怒火中烧,说道:“钱威一,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钱威一说道:“没想到朱大人如此沉不住气,古来成大事需得一步一个脚印、藏着掖着,不可操之过急,如若不然,反引来杀身之祸。今日朱大人如此行事有三不该。一不该命令副将不开寨门,副将是城西大寨的副将,朱大人对外说辞是副将不听将令,但明眼人看就知道是受朱大人指示,只怕杨行密此时也是心知肚明。第二不该杨行密车驾已到城西大寨门前视而不见,反倒要符节,这不是向群臣展示朱大人有司马昭之心吗?三不该诬了安仁义,看似除掉了安仁义这个心腹大患,却也逼得杨行密不得不对大人动手。”
朱延寿不以为然,笑道:“钱兄将杨行密想的过于精明了。杨行密如似钱兄这般精明,只怕不会杀了自己的前驱,更不会将安仁义关进刑部大牢。如今安仁义被抓,城东大寨已然不再是障碍。”钱威一见朱延寿并不醒悟,便接着说道:“大人有所不知,当时形势杨行密必然算定大人手中掌握城西大寨,而自己身处敌营,用一个小小前驱项上人头买大人一个安心,换一时平安,确是十分划算。如若杨行密信了大人所说,为何不立斩了安仁义?”朱延寿脸色稍变,说道:“如今杨行密双目失明、命不久矣,城西、城南大寨又皆在我们之手,他就算察觉了事情不对,又能如何?”钱威一说道:“当前杨行密还是吴国之主,各路刺史依然听从杨行密号令,古人言:‘以一国抗一隅,未有不胜’,朱大人手中的城西、城南大寨可对抗得了整个吴国?况大人身处扬州,远离寿州,无尺寸之地可以立身,如真是刀剑相向,大人何以自处?”朱延寿听了钱威一分析,拍着大腿说道:“王总管你害了我啊!”王总管心中不忿,说道:“那如此形势,钱军师可有什么良策?”
钱威一不理会王总管所说,回禀道:“我怀疑杨行密一直装双目失明,故意引大人出手,好除之后快。如今,大人需得刺探出杨行密双目失明的真假。如是真,则因早早行动,快刀斩乱麻,一举夺了这吴王之位。”朱延寿说道:“杨行密已经双目失明三年,此事难道还有假?如真是假又当如何?”钱威一低头不语。
话说城西劳军之后,杨行密带着大小官员回到宫中,把安仁义、严泰、花未晞下了刑部大狱,事后吃了晚饭,天色渐晚,黑夜笼罩了整个宫殿,几朵云彩遮住了月色,宫殿内出奇地黑,一个太监手提花灯搀扶着杨行密往寝宫走去。一个不小心,杨行密撞到了身前的金丝楠木柱子,吃痛地“啊”一声,太监惊慌失措地跪倒在地,哭声道:“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天黑竟没看清门柱,害的吴王撞了,奴才该死!”杨行密说道:“今晚天黑的很,不怪你。”太监见杨行密并不怪罪,便起身拍了拍尘土,扶着杨行密进到了寝宫。
杨行密被扶至一张梨花木椅子前坐下,说道:“给我一张手帕。”“诺。”太监从身上掏出一张白色绣花手帕递到了杨行密手中。杨行密接过手帕说道:“你先下去。”太监慢慢退出了寝宫,关上了宫门,便离开了。杨行密手拿手帕捂住嘴咳嗽了几声,拿将开来时,发现一团鲜血染红了手帕。杨行密看着鲜红的血渍,沉吟了半晌,自言自语道:“看来我时日不多了,是该整顿整顿了。”说罢,走到一盏琉璃灯前,借着灯火,将带有血渍的手帕点燃,看着燃烧地手帕,说道:“手帕本是擦拭污渍所用,既然脏了,就应该烧掉!”
天斗出横,东方欲白。杨行密正在龙榻上睡得正酣,身边躺着朱氏。这朱氏花容袅娜,玉质婷婷,髻横如云,眉似柳叶,面如桃花,腰如约素,秀色可餐。深夜中,朱氏偷偷摸摸翻出龙榻,拿起床边长袍披在身上,粉红亵衣似漏未漏,走到门前,对着门前守卫说道:“你们先下去吧。”两名守卫依照指令,撤出了宫门。不一会儿,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的嫪越来到宫门前,轻声轻脚推门而入。朱氏见此人来了,脸上生出一片红霞,低声埋怨道:“死鬼,你怎么才来啊?”嫪越上前一把抱住朱氏,上下其手起来,说道:“小可人儿,我一路往这赶,辛苦的很。再说路上不得避开些人,如被吴王发现,咱只怕有死无生了。”朱氏似嗔似笑地打了一下嫪越的手,说道:“那可未必,只怕他这吴王过了今日之后就不再是吴王了。”嫪越好奇问道:“难道朱大人要动手了?”朱氏点头低声说道:“我大哥计划明日动手,到时这吴国就是我朱家的,你我也不必再如此偷偷摸摸、提心吊胆,让我哥给你封个刺史,我便嫁到你封地去如何?”嫪越喜不自胜,说道:“天下没有这般好事了。”说罢,在朱氏身上亲了起来。朱氏轻轻地打了嫪越脸一巴掌,说道:“心急的死鬼,杨行密就睡在一旁,你也不怕事情败露。”嫪越捂着脸,笑嘻嘻地看着朱氏。朱氏拉着嫪越的衣角,走到了寝宫边角处的一张方桌前,褪去了身上的长袍和粉红亵衣,娇嗔道:“还不快些。”嫪越急忙脱了衣衫,如猛虎饿狼一般扑向了朱氏。正似交颈鸳鸯戏水,并头鸾凤穿花。罗袜高跳,肩胛上露一弯新月,金钗倒溜,枕头边堆一朵乌云。富贵廉耻皆不要,真实偷期滋味美。
二人云雨才罢,正欲各整衣衫,只听得杨行密突然在龙榻上坐起身来,说道:“梓童,与我到杯水来。”嫪越惊慌失措,急忙翻窗而出,朱氏慌忙整顿了衣衫,疾步走到杨行密身前,说道:“好的,吴王,我这就给你斟杯水来。”杨行密咳嗽两声说道:“我怎么听了屋内除了你还有其他人?”朱氏急忙回道:“哪有其他人,宫内守卫如此森严,怎么有人进来?”杨行密说道:“那可能我听错了。梓童大半夜不睡觉,起身作什么?”朱氏回道:“刚刚有些凉,我起身关了窗户。”说话间,关了嫪越打开的窗户,顺手拿起一个茶壶倒了一杯茶水递到杨行密手中,杨行密接过茶盏,咕噜咕噜喝了几口,便依旧倒身睡去了,朱氏惊魂未定,一夜无眠。
铜壶漏尽,铁马摇曳。深夜之中,众人皆安然入睡,刑部大牢中安仁义却始终无法入眠。安仁义盘坐在一堆茅草之上,一旁睡过一觉的严泰翻起身来,见安仁义依然没有入睡,说道:“大哥怎么还不睡?”安仁义满脸愁容道:“我被吴王抓了起来,关进刑部大牢,如今城东大寨群龙无首,只怕朱延寿趁机兴风作浪,到时我吴国只怕又要血流成河了。”安仁义拍了拍严泰肩膀,说道:“小兄弟,叹吴王听信奸佞之言,迫害忠良,牵连与你,大哥我十分内疚。”严泰笑着说道:“大哥不必忧心,咱们今日在这牢里住一晚,明日就无事了。”安仁义说道:“小兄弟也别宽慰我了,只怕吴王被人蒙蔽,你我不久就成刀下冤魂了。”严泰笑道:“我看未必。”安仁义奇道:“何出此言?”严泰说道:“当时形势,吴王身处朱延寿大寨之中,不能打草惊蛇,只能用前驱人头买一日平安。吴王若真信了朱延寿之言,为何不直接杀了你我?吴王看上去将你我关入大牢,实际上却是保护你我免受朱延寿暗杀。大哥放宽心,稳稳睡上一觉,只怕明日天明,吴王就要召见你有要事托负。”安仁义将信将疑,却也别无它法,只得歇了。
次日,天刚初明,太阳已早早挂在天上,看来又是炎热地一天。一个太监匆忙走进刑部大牢,拿出虎符道:“见此虎符如见吴王。”牢中狱卒急忙跪下,太监挽起浮尘,说道:“吴王有令,众狱卒退出刑部大牢,今日之内不得靠近。”众狱卒诺了一声,纷纷退出刑部大牢。太监在墙上拿下了一串钥匙,疾步走进了阴暗潮湿地甬廊,来到一个牢门前,拱手道:“安大人受苦了。”安仁义从梦中醒来,抬眼见是吴王身边的李总管,便站起身来,说道:“李总管怎么有空来此晦气之地?”李总管道:“吴王要召见,我奉命前来接大人。”说罢,便急忙打开牢门,解开了安仁义、严泰、花未晞三人的手镣脚镣。
李总管带着三人出了刑部大牢,向城外走去。安仁义好奇道:“李总管,不是吴王要召见我们?这个方向不像是去宫中路,反倒像是出城。”李总管笑道:“吴王不必担心,城外有一条暗道可直通宫中。此时宫中朱延寿眼线众多,不方便直接进入,只能委屈安大人与我从这暗道走一遭。”安仁义听此,便不再多言语,紧随着李总管身后。四人出了扬州城,走了一里路,来到一个枯井旁。严泰见着枯井正是不久前躲避悍匪时的枯井,笑道:“竟有如此巧合之事。”安仁义问道:“什么事如此巧合?”花未晞将前几日被悍匪所追之事讲述了一遍,安仁义听后说道:“那位高僧不知何许人也,武功如此高强,只叹没机缘见上一面。”
李总管从怀中拿出一条长绳,栓在了一棵大树上,四人先后顺着绳索下到了枯井之中。枯井中残留着火灰的痕迹,李总管透着井口照下的几缕亮光,走到井壁前,转动了壁上一个凸起,只听得“轰隆隆”地声响,井壁上破开了一个大洞,透出了一条长不可测地黑暗通道。李总管转过身来说道:“这就是通往宫中的暗道,大家请随我来。”说罢,带着众人走进暗道之中。进入暗道数丈之后,便见不到一丝亮光,众人在暗道之中摸索前进。大约过了一炷香时间,严泰伸手摸出前方横着墙壁,说道:“莫非已经到了。”李总管挤到众人前面,双臂高举过头顶,顶开了一个石板,说道:“正是。这就是出口。”众人跟着李总管爬出了暗道,出口边正站一人,正是杨行密。
李总管跪拜道:“吴王,安仁义等人我已带到。”杨行密点了点头,说道:“你先退下。”李总管称了声诺,便退了出去。严泰见杨行密已然没了前日的病态,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俨然不是瞎子,浑身上下透着杀伐果决地王者之气,若不是亲眼所见,严泰断然不会认为前日城西大寨中的吴王和面前站着的是同一人。安仁义见了杨行密,悲喜交加,慌忙叩首道:“大王没有眼疾,我吴国有救了。”杨行密伸手搀扶起安仁义,说道:“安大人,孤城西大寨之时有诸多不得已,委屈你了。”安仁义站起身来,说道:“大王竟然没有眼疾,为何却又要装瞎?”杨行密将双手背于身后,慢慢踱步道:“哎,这眼疾装得也三年有余了。人在高位,如浓雾遮眼,难以看清事物本相,孤装瞎一来外防朱温、钱缪之辈,使其麻痹大意,二来内辨群臣,看清谁忠谁奸。”
安仁义说道:“大王可知朱延寿结党营私,祸乱国家,残害百姓?”杨行密点头说道:“孤早已知晓。”安仁义说道:“大王可知朱延寿已有谋反之心?”杨行密停下脚步说道:“此人胆小怕事,好谋无断,刻薄寡恩,难以成大事。”安仁义说道:“大王竟然心里如此明白,为何要还将大权落入他手?”杨行密说道:“古来君王既要用的忠臣,也要用的奸臣。孤既装眼疾,必然不能处理国家大事,国家大权只有放在这等人手中,才能放心。”安仁义吃惊道:“既要用的忠臣,也要用的奸臣?古来奸臣只有误国,为何还要用?”杨行密笑道:“爱卿可听得‘水至清则无鱼’?古来朝中忠臣自成一党,奸臣自成一党,皇帝高高在上只需做个执棋者,平衡双方势力,才能保的国家安稳。奸臣百姓恨之入骨,忠臣耻于为伍,权力放入这等人之手,自然说给就给,说收回就收回。帝王之家也有些难以启齿之事,忠臣受礼仪教化,不屑干此等之事,也只有假借奸臣之手,污了奸臣保全了帝王。爱卿听得百姓骂安禄山、骂杨玉环,可听得百姓骂唐明皇?”安仁义哑口无言,默不作声。
杨行密接着说道:“朱延寿近年来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家中财富可抵几年国库收入,抄了他的家,吴国五年之内不会再为银子发愁,有此钱财,到时伐钱缪、征马殷、灭高季兴、诛王建,与朱温划江而治,待到时机一统天下,未为不可。”严泰说道:“好个帝王心术!”杨行密看着严泰和花未晞,笑道:“朱爱卿,还没介绍一下这位英雄少年和这位美丽女子。”朱延寿指着严泰和花未晞说道:“这位是严泰,这位是花未晞。前日,臣在扬州城里恰巧碰上王总管骑马冲撞行人,臣上前制止救下,结识两人。如今看来,这姑娘武功高强,倒也不用臣出手了。”杨行密深沉地看着严泰和花未晞二人,眼中有提防之色:“那也未必,如不是你出手,怎么会结识二位?这小兄弟看待事物清楚明晰,这位姑娘武功高强,幸得被你结识,若投了朱延寿,反倒不好处理了。”
杨行密接着说道:“安仁义,孤有要事委托于你。”安仁义跪拜道:“请吴王示下。”杨行密说道:“安仁义听令!”安仁义说道:“臣在!”杨行密从怀中拿过一个兵符,递到安仁义手中,说道:“此兵符可调扬州城内所有兵马,命你现持此兵符,火速赶往城东大寨,夺回城东大寨控制权,然后带着城东大寨兵马赶到宫中护驾。路上如有碰到朱延寿、田馥一干人等,就地斩杀,无须禀报!我料定此二人今日必反。”安仁义拱手道:“臣遵命!”杨行密扶起安仁义,深情地说道:“爱卿,孤现将身家性命托负于你,希望你不辱使命,平安归来。”安仁义说道:“臣一定完成任务。”说罢,转过头看了看严泰和花未晞二人,杨行密知其含义,说道:“爱卿不用担心,我会将他二人带在身边,保他们周全。”安仁义听此,便不再言语,带着兵符迅速离开宫殿,向城东大寨而去。
安仁义带着几个将士,来到城东大寨,走近主帐门口。此时,主帐中二十多个偏将分列两侧,中间站着朱延武、朱延亮二兄弟。安仁义大步走进帐中,总偏将见了,皆拱手道:“大人!”’朱延武怒道:“哪里来的大人?安仁义你通敌卖国,被吴王关入刑部大牢,擅自越狱,不去逃命,竟还敢来此地!”安仁义哼了一声,走到朱延武面前,大声说道:“我奉吴王之命,重新接管城东大寨。你们兄弟二人算什么东西,城东大寨还没你们说话的份。”朱延武、朱延亮二兄弟向前一站,说道:“我兄弟二人奉吴王之命接替你的职务,今日之后这城东大寨再没有你这个将领。”说罢,朱延武从怀中掏出一张黄绫。安仁义接过黄绫,看了一眼,便将黄绫扔到了地上。朱延武大怒道:“此乃吴王旨意,你竟敢随意侮辱。”安仁义大笑三声,说道:“吴王?大印掌在朱延寿手里,找人写几个字,盖了大印便在这里假称吴王旨意。吴王今日一直与我大雄宝殿之上,何来的时间去文殊阁起草旨意?”安仁义从袖中掏出兵符,说道:“见兵符如见吴王。众将听令,吴王有命,朱延武、朱延亮二人与朱延寿蓄意谋反,给我抓起来砍了。”
朱延武、朱延亮心中慌乱,急叫道:“安仁义你敢,我们有吴王诏书,你竟敢乱杀朝廷命官。”安仁义冷笑道:“吴王已赋先斩后奏之权。”几名将士赶到台前,将朱延武、朱延亮捆了起来,朱延武大叫道:“我们是朱大人的亲信,你们竟敢杀我?”安仁义叫道:“杀的就是朱延寿的亲信,来人啊,押下去。”朱延武、朱延亮被押出主帐,就地正法。
安仁义快步走到台上,面对众将说道:“吴王乃圣明之主,假装眼疾,韬光养晦多年。朱延寿无知鼠辈,假借吴王之令,祸乱国家,残害百姓,天理不容,今日竟有谋反之心。吴王将扬州兵马交于你我之手,望众将士勠力同心,剿灭朱氏叛贼,保我吴国江山。事成之后,各位皆有护国之功,到时我请示吴王为各位加官进爵。同僚们,上天赐予此良机,大家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时候到了。”台下众将士高呼道:“誓杀朱延寿,保我吴王江山。”呼声天震地动。安仁义清点武器兵马,带着众将士向宫中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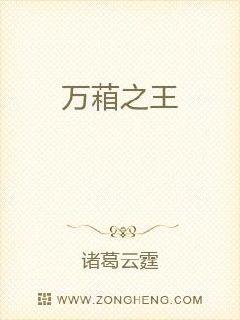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