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起山河九万里》最新免费章节第二章别亲再远游
第二章 别亲再远游
余青衫本是江南人,赴京赶考之前与邻村女子定下终生。约定考成之后,回乡成亲。不过头年因广鸿城中显才华,打了京中一贵公子的脸,故被下了绊子,该年没能参考。
恰在途中与明鼎庄庄主结识,无依无靠之时得其相助,留在广鸿城苦读,终于三年后骑着戴红花的高头大马一日看遍京城花。此后留在京中任职,更是以清廉秉公理在广鸿城里颇具佳名。
余青衫不止一次想过返乡,可无奈广鸿城中乃天子脚下,并非寻常来去自由之处,返乡之事只能一拖再拖。直到一日,在京城遇见乡中人,委婉聊及女子,方才得知早在其考中之前女子便因病含恨而终,至死未能等到心上人,也未曾听到其登榜的消息。
余青衫只听得“临死未嫁”四字,常心怀愧疚,彻夜难眠。后终辞官回乡祭拜,却也无颜再待在乡中,一路兜兜转转便来到了这小程村。
而后明鼎庄庄主夫妇据余青衫来信地址寻来到此处,将尚处襁褓的余念白托付给他。明鼎庄庄主姓于,与余青衫同音不同字,不过二人相熟之后常以本家兄弟互称。庄主妇人姓白,故而将孩子托付给余青衫之时,道及名姓,只说:“姓随着余兄的余便好,有个音留个念想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名,叫做念白吧。”
天禄十五年开春,北齐来信,武道修为一品境,天乾榜上位列前十的明鼎庄庄主比武时被误伤,伤及经脉,不治身亡。朝中闻信再降旨,歌其“为国捐躯,当为天下之典”。
只是日后不久,明鼎庄被其他江湖门派瓜分取缔,朝中从未有任何声音传出。
余念白双膝跪地,坟前土被跪出两个明显陷下去的坑。老人知晓其心中一时间定是难以接受,便也不在一旁打扰,从兜里掏出一封封存得完好得信笺递给他:“这是你爹临走前写给你的信,嘱咐我把事情都告诉你之后再把信给你看。”
说罢,拍了拍余念白的肩头,转身就欲离去。可刚走了没几步,不知是想起了什么,又停住步子,回头看看那跪着的少年,叹口气,又扭过头去,背着余念白说道:“你去从军的时候,你爹就和我商量等你回来就把这些事儿都告诉你,但是他没能等到那一天。
你回来的这三年,我也一直想着找个机会跟你说说,但是老头子我没有你爹的口才,不知道怎么样说得才能让你好接受一些,才能不让你那么难受。
我就一直等着一直等着,眼瞅着守孝期过了,你又要出去了。思来想去只能今天跟你说说了,我怕再拖下去,老头子我怕是熬不过时间了。”
老人说完欲走,又被余念白叫住:“白爷爷,我,亲生爹娘,就埋在这里面吗?”
“尸骨未寻,这里只是衣冠冢。”
余念白没有再回话,只是在坟前长跪。突然被灌进这么多往事,撑得他脑子发涨,仿佛要裂开一般。
跪了半晌,白爷爷早已经走远。余念白揭开那羊皮纸信封,抽出封存其内三年来从未打开过的信纸。
熟悉的字迹跃然于眼前,“吾儿念白,展信安。”
只几个字,眼泪就不争气地滚落。
余念白擦了擦眼泪,不让泪水滚落打湿信纸。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爹已经不在这人世间了。原谅爹没能看到你娶媳妇儿,也没能帮你带孩子,更原谅爹把你的身世瞒了这么久。
你也莫要去怪白爷爷,他十数年如一日地陪护在咱们爷俩身边,已然是极大的恩情了。况且,有关于你的身世所牵扯的又极为复杂,我们也是思索再三才决定等你长大以后,有能力保护自己了,再告知于你。
没能亲口告诉你你的身世,这是爹的一大遗憾,因为没能亲眼见证到你真正能够保护自己的时刻。而现在当你从白爷爷那儿知晓真相,打开了这封信,我十分欣喜,说明这是白爷爷对你现在的能力的认可。
你的亲生爹娘是一对令人艳羡的伉俪,郎才女貌仿若是因他们才生出的词。他们当年实属最无奈之举,不然也不会将尚在襁褓中的你交予我这么一个外人。你的身上流着他们的血 ,你应当因他们而自豪。
江湖路远,出门在外自己注意安全。关乎你的身世之事,在我看来暂且还是留存在你心里,这样对你自身也更安全。这也是白爷爷从未教过你本家功夫的缘故。
思来想去,觉得你定是心中有判断,不过犹豫再三还是再唠叨几句。明鼎庄之事乃一家之主为其氏族坐稳皇位所行制衡之事,你心中有怨爹能理解。不过你始终须谨记,忠国之血不能凉。
我至今都还记得你爹娘把你送过来的时候,他们对我说:‘只要他还活着,我们于家的血就还是热的。’这话我对你说来也是一样,只要你好好地活着,不行苟且事,我们老余家的血也还是热的。
人之所处即是江湖。入得江湖容易,苟活也非难事,守住本心才最为可贵。
父青衫,天禄三十年七月留。”
余念白跪伏在三座坟之间,再起身已是哭成泪人。
他小心翼翼地将信纸折好放回羊皮纸信封中,用力捏住封口再小心翼翼地放在衣服内层的兜中。
郑重地冲着面前这座合葬墓重重磕了六个响头,又挪到余青衫坟前磕了三个。
起身擦干泪,目光停留在三个微微凸起的坟包之上,敛去哭腔,轻声道:“您三老睡好,孩儿走了。”
回到村里,余念白并未再去白爷爷的小屋,而是径直回了自家小院。把行囊收拾好放在门口,明早提起来便能上路。
简单洗漱完,余念白便带着复杂的心情浅浅地睡去。再醒来,也不知道屋外时辰,只是看着仍有星点挂在天边。
睡是没有了睡意,想着趁天还没亮就早些出发,免得被早起的村民瞧见了,到时候又是徒增一番伤感。
余念白背着行囊行至河边小屋,屋里还亮着灯。不知是早起点的灯,还是一夜未熄。
他轻手轻脚地推开屋门,随着上了年头的老门“嘎吱嘎吱”刺耳的声音,从仅打开的一条缝中挤了进去。
一进门内,屋里桌上竟摆了两只碗。白老爷子就靠在一旁的躺椅上闭目。听见开门声,眯着眼看来人,迷迷糊糊道了句:“来了?我去盛粥。”
余念白心情有些复杂,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愣愣地点点头,便放下行囊坐在桌边候着。
片刻,老人就端了两碗粥上来,嘴里还“呼哧呼哧”地叫着烫。
“喝完热粥,再吃俩馒头,暖和的好赶路。”说着直接抓了一个馒头塞给余念白。
“快尝尝我的手艺,都已经几十年没蒸过这玩意儿了,弄了半宿,看看退步了多少。”
余念白没说话,接过馒头一口塞进去半个,又低下头“呼噜呼噜”一口气喝下去一碗刚盛上来还冒着热气的粥。
老人笑骂他饿死鬼投胎,可在一旁看着他一口气喝完,还是抱着期待地问道:“再来一碗?”
一碗喝完,余念白愣了愣,还是抬头将碗递给老人。
白爷爷给余念白又盛了一碗粥,没有坐下,而是转身回屋拿了一只书匣。
“我东西不多,不用拿这个装。”余念白有些哭笑不得,复杂之情也渐渐淡了些许。
“你打开。”老人也是轻笑,还是那副爱卖关子的模样。
余念白顺着话打开书匣,里面并不是如他所想空荡荡的,也没有装满了行李,却是靠着书匣内壁,斜立一柄长剑。
“试试。”老人依然嘴角挂笑,抬抬下巴示意他拿出来试试。
从剑鞘中微微抽出一寸剑身,却已在油灯映照之下射出一道刺眼的光。剑握在手中,无论是剑重还是手柄长度,都是恰到好处。
完全抽出剑身,揪下一根头发,只放在剑刃上轻吹一口气,那根头发丝儿就已然断成两截。
剑是好剑,只不过和他以往使的剑又有些不甚相似之处。
余念白在军中摸过的剑不少,军中的剑因常年被血肉磨砺,时日久了其上或多或少的都会染上些寒气。但是手中这柄剑并没有这般感觉,估摸着应是一柄新剑。
老人好像知晓余念白心中所想,还没等他开口发问,就抢先说道:“自打你寄信回来说习了剑,我便想着打柄剑送给你。送给我们家念白的剑那肯定不能是上不了台面的货色,我寻了个老友,花了几年功夫才打出来这柄剑。
我不是很懂剑,但是那个老家伙倒是个行家。他耗费这等功夫打出来的剑,应该是能凑合着给咱家念白用用了。”
老人说得是云淡风轻,但余念白已是能估摸到手中这柄剑的价值。心生感动自是当然,不过自小绕老人膝下长大,两人虽无祖孙血缘,却早已有了超越祖孙之情,再说那些个感谢的话,倒显得过分矫情。
余念白收剑入鞘,来回地摩挲,轻叹道:“好剑”。便拍了拍被剑鞘包裹的剑身,迎向老人的目光,嘴角微动,想说点什么,到了嘴边只化作淡淡一句:“收下了。”
收下剑吃过早餐,听老人有的没的唠叨了几句。老人这两天的话较之以往多了不少,余念白倒也不觉得奇怪和厌烦,他只是觉得有些不舍。
老人靠在椅背伸头望了眼窗外,天际已灰蒙蒙的带了些光亮。他扶了一把桌子站起身,到余念白身边拍了拍他的肩:“小伙子,出门在外万事小心,累了就回来跟着老头子我学钓鱼,到时候再请赵大娘给你做个媒,讨个媳妇儿。”
说罢,也没等余念白应答,就收拾起桌上的碗筷转身去洗,不再说话。
余念白望着老人的背影,才发现这常年坐在河边的老头子也佝起了背。冲着背影,他轻声问道:“白爷爷,你以前在明鼎庄的身份是?”
老人洗碗的手一顿,随即又恢复常态,“白家随嫁老仆。”
余念白点点头,没再言语。背上书匣走到门口,又转过身冲着屋内老人的背影,跪地磕了个头。
天色尚早,不说是小程村了,就是顺着官道一直走到日头出来,也不曾看见几个人影。
早在守孝期间正式决定要好好地闯一闯江湖之后,余念白就一直盘算着行程。
在军中的三年,虽说艰苦危险,但是刀口舔血的日子却也正好结识了一帮还算是交心的朋友。守孝三年,虽然偶有朋友寄信,但终究还是许久未见。
有时夜里梦见一起从新兵小卒一同长成平叛军中杀敌好手的日子,不免得在醒来之后有些怀念,又有些怅然。
思来想去,所谓的“闯荡江湖”在余念白的盘算之下渐渐就演变成了拜访友人们的旅程。
出小程村的时候正值入了秋,余念白心里想着倘若此刻再北上,那估摸着等到寻得那几个家伙的时候,定是已经入了冬季。明明人还未向北而行,但一想到草原的冬天,禁不住的还是浑身一哆嗦。
盘算一番,还是决定先南下过冬,等来年开春,天气回暖之时再北上,反正他的时间多得很。
小程村地处中原,属河南道安阳州。听着好像不远,但是算起距离,寻常人光是在官道上就要走上五日有余。就是余念白在军中磨练,脚程较之常人要快些,可也走到第三天午后才到了安阳城下。
安阳州虽属河南道七州之一,但也几近于是七州中最小的一城。走在安阳城主道上,来往人也多也不杂。除了本城的住民,也就都是些讨生计的行脚商和佩刀佩剑的护镖人。
行脚商们大多操着一口江南口音,靠着墙根坐在路边向往来行人吆喝。江南道那儿的人做娃娃,香囊这类小玩意儿总是更手巧一些。并且总是会有行脚商把苏州府里近来卖得好的式样带来。
时间久了,在安阳城这般人口并不能算上众多的地方,凡是有操着江南口音的商贩,他们的摊子旁定是围满了人。
就算是不买,但是能这般凑近了解个眼馋,倒也心满意足。
余念白向来对这种摊子没什么兴趣,并且自打从江南道那儿来的军中伙计带着不屑的冷哼中知晓这些行脚商几乎都是翻倍定价之后,他就更不愿意在这些江南行脚商的铺子前驻足。
有这个功夫,他还不如找间茶楼,要一碗茶,几个吃食,寻一个楼上靠栏杆的座儿,听上半日说书或是小曲儿。
这个习惯自打认识了几个字之后便有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都还只是得空去旁边县里。县里也并没有一个像样的茶楼,就只是一个露天的卖茶铺子,摆了几张桌子椅子而已。
在最前一排的桌椅之前约摸五步,又摆了一张小方桌,其上铺了台布,又摆置了几件类如折扇,抚尺这类的小物件。
每日固定那么几个时辰,会有个说书先生端了个茶盏,不知从何处现身,穿过人群,先是放下茶盏冲着台下候着喝茶的茶客作了个揖,随即走到桌后,一撩长褂坐下,便是说起了今天的书。
都说安阳城小,但是相比起来,小程村边上的那个县就更是不大。像这样简陋摆置的卖茶铺子,整个县上也不过就一家。
余念白自幼在那儿听说书,虽说其间也换过几个说书先生,但他毕竟从茶铺老板家的儿子背包上学堂一直听到其成亲,日子久了,听来听去也就是那么些故事,甚至于其中大多余念白都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
故而余念白凡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儿,第一件事便是奔着当地的茶楼或是听说书的地儿。这个习惯一经养成,便是致使其评价某个地方的印象成了在这儿听的第一场说书如何。
说书听得多了,余念白禁不住去想是不是这天下的说书先生的祖师爷都是一人,要不然也不会总有那么几个话本都是一模一样的。安阳城茶楼里的这位自然也是如此,。
不过,到底安阳城和县城还是有着分别的,这儿的说书先生倒也是能讲些他从未听过的话本。吃了几盏茶的功夫,听了几个新鲜话本,对于余念白来说,那一这趟就不算是白来。
现在未到饭点,想找个地儿坐着歇息或是围一桌闲聊也就只能来茶楼。而安阳城里因地处河南道较偏之地,加之属地又少,人口以及往来赶路行人都较其他几州要少些。
赶路途径此地,更多的还是北上的护镖人。
余念白此刻坐在茶楼二楼靠着栏杆的座,楼上除了他还有几桌客人,看着他们的模样以及间或听见话中所聊,便能大概知晓都是镖局的汉子。
说书先生下台歇息的间隔,余念白闲坐无事,便不自觉地听着旁桌几个汉子拉话。
好像是听见汉子们口中有“马市”这类字眼,余念白初听还不在意,忽地打了个激灵。心道自己这般行路,路途遥远,还是得买匹马来得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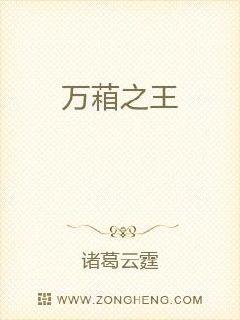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